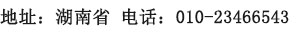小说连载:出门寻死(1)
小说连载:出门寻死(2)
小说连载:出门寻死(3)
13
婆婆又叫了一声,做不做饭,总得应一声吧?你要不做,我来做就是了。刘建桥说,狗日的,你还不动?何汉晴说,建桥,我蛮不想活了,我去死了算了。刘建桥心在不焉道,你?全世界都死绝了,你都还剩在屋里,我还不晓得你?何汉晴叫刘建桥的话说得一愣。心想,这是么话?你以为我不敢死?刘建桥又说,老子刚才没有打你,是让你。你要再闹得中饭都要姆妈做,等一下不把你往死里打我不姓刘。何汉晴说不出话来。刘建桥的话并不重,甚至还有一些淡淡的、漫不经心的味道,像是没有经过刘建桥的脑子,也没有经过刘建桥的喉咙,从窗外飘进来一样。何汉晴想,这样跟你过日子,我何必要你打死,我自己去死不更舒服些?你当我没有想清楚?我现在这个样子,死了不是比活着强?公公一脚踢开门,他的声音震耳欲聋,这是搞么事名堂呀!还想不想过日子?何汉晴无奈,她只能爬起来。她明白,就是自己真想死,还是得把这顿饭做好了才能去死。饭菜都端上了桌,公公婆婆已经坐好。何汉晴把刘建桥喊出来吃饭。建美也刚好在开饭的时候回来。建美在附近一家超市当出纳,为了省钱,她总是回家吃饭。何汉晴盛好四碗饭,自己却朝卧室里踱去。建美说,嫂子,你不吃饭?何汉晴无精打采地说,我没得胃口。婆婆说,你这是做给哪个看啦?何汉晴说,我不做给哪个看,我不想吃也不行?公公说,这年头,真是板眼(本事,武汉方言,下同)大,有吃有喝的,一个个都还活得不耐烦。何汉晴说,我是活得不耐烦了。婆婆说,你想么样?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建美笑了起来,说,嫂子,你莫学珍珍咧。医院,医院门口,累得快断了气。嫂子你有珍珍两个肥,我背你,没有出家门,我压也被你压死了。刘建桥说,莫耳她(不要理她———编者注)。她刚才说她想死,我一个字都不信。她这种喜欢到处岔的人最舍不得死。就是小鬼把她捉到了阎王爷跟前,她两脚就把阎王爷踹在地上,自己跑回来。她这半生才只岔完了一条街,还没有把汉口都岔到,她舍得死?何汉晴没有理他们,她径直进了房间。屋外的说笑声隔着门板传了进来。建美大笑出声,建美说,哥,看不出来,你还有点幽默咧。婆婆也笑了起来。婆婆说,长江上没得盖子,铁路边没得警察,厨房里有刀,药店里有药。挡别的挡得住,挡死是挡不住的。也不晓得汉晴会选哪样。建美又笑,说,我嫂子呀,走到江边,一看,咿呀,这好的江水,死在里面会搞脏的,跳不得;走到铁路边,一看,咿呀,压死了我是小事,这不是害了别个司机?这撞不得;回到厨房拿起刀,一看啦,砍缺了口子,明儿过年婆婆剁肉刀子不快了,这用不得;最后跑到药铺里,一看,死个人买药还要花这么多钱,鬼才买它。嫂子转遍了汉口,硬是找不出个法子让自己死。建美的一番话,说得连板着面孔的公公也笑了起来。婆婆说,莫以为死是一个简单的事。人一辈子只有一死,这死也是件要水平的事。这种事,汉晴这样的粗人,想都想不到。建美说,姆妈说的是。就嫂子这个个性,哪里适合死。何汉晴倚在卧室的窗边,眼睛望着外面,耳朵却在听着。听完婆婆的话,何汉晴冷冷地笑了笑,心想,你们都不信我会死?人想死了,还要么子水平?一口的屁话!这回我非死给你们看一下。我在你们刘家这多年我也受够了。老公下岗挣不回钱,我就出门去挣。我伺候公婆,照顾小姑,生养儿子,屋里的重活轻活我一肩担了。你们眼睁睁都看到我做这做那,却从来没有哪个说过我几句好话,反倒是个个瞧不起我,嫌我是个粗人。我只不过上厕所时间长了一点,你们就对我这样。我是故意的?我有病,我比你们还难过,你们哪个替我想了?我就是一个粗人!我不会看书,不会拽词,更不会写文章,更不会拐弯损人。但是我也还没有蠢到连死都不会吧?何汉晴越想越气,越气就越委屈,越委屈就越觉得自己这辈子过得辛苦。突然间她觉得她一刻都无法继续在这里待下去。何汉晴对自己说,我要争口气,我今天就死给他们看!她想时,便迅速地给自己换了一件衣服。换好衣服,她照了一下镜子,觉得这样去死也还体面,便拉开门往外走。建美见她出来,忙说,嫂子,还是来吃一点吧。何汉晴说,你们都说我不会死,我这就出门寻死去!何汉晴跨着大步往外走。她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我非死给你们看看不可。刘建桥的声音跟在后面。刘建桥说,我还不信你会去死咧。那我就等着看。建美还在笑,建美的尖叫声追得更远,嫂子,找到了一个好死法,打个电话跟我通个气,我好帮你参谋一下。何汉晴在里份的熟人真是太多了。何汉晴从南岸嘴嫁过来已经二十几个年头。她看里份街坊的婴儿长成小伙子,看见小伙子成家生子,看见叔叔阿姨成爹爹婆婆,又看见爹爹婆婆一个一个地在里份的门边消失。时间快得她自己都记不得了。
14
何汉晴走出家门才几步,就有人跟她打招呼。先是对门的陆伯。陆伯说,汉晴,好久没有来我屋里坐了,你陆妈前两天还跟我说,几天听不到汉晴的大喉咙还真有点不舒服咧。何汉晴心里郁闷,又不能不搭话,便勉强地笑了两声,说陆妈的腰好点了没有?陆伯说,睡都睡了三四年了,指望好是好不起来的,不变坏就是福。老太婆就是想有人去跟她说话,汉晴你得空就到屋里来坐一下,她蛮喜欢听你说街上那些七里八里的事。何汉晴嘴上说好,心里却想,过不了几个钟头,我这一生的事就都忙完了,每分钟都得空。可是我哪里还去得成?想罢就觉得有点对不起陆伯和躺在床上不能动的陆妈。这边陆伯的话刚说完,跟着是隔了几道门的朱婆婆。朱婆婆披件花棉袄正在屋角的墙边晒太阳。见汉晴,扯着老嗓子喊道,汉晴嘞———伢,快点来,正在想你,你就来了。换在平常,汉晴一听喊,便会快步走过去。可今天,何汉晴有些倦怠。朱婆婆又喊,汉晴,伢,你快过来!我还想差人找你去咧。何汉晴无奈,只好过去。何汉晴说,朱婆婆,么事?朱婆婆眯起眼,递一个捞耳勺,说我耳朵痒死了,你赶紧替我掏几下子。何汉晴说,改天好不好?我今天有点事。朱婆婆笑道,你那点事我还不晓得?要不了几分钟,耽搁不了你。我等你等了个把钟头。我屋里爹爹想给我掏,我把他推回去了。他那个粗手,若把我耳朵掏聋了,我还划不来。爹爹说,你耳朵蛮金贵?还得派专人来掏?我说,我耳朵就是金贵。除了汉晴,别个都不够格。何汉晴苦笑道,朱婆婆,你这样抬我的桩,我哪里消受得起?朱婆婆说,看你说的,一条街,还就是你消受得起我的夸。你嫁过来,我这耳朵就没有换人掏过。快点快点,我痒死了。何汉晴只得接过挖耳勺,对着阳光,为朱婆婆掏了起来。跟平常何汉晴喋喋不休地和朱婆婆说话的状态比,今天的何汉晴有些沉闷。朱婆婆说,汉晴,伢,你今天心里有事?何汉晴说,没得事。朱婆婆说,你今天跟往常不一样咧。按说你那个嘴巴是关不住的呀。何汉晴说,没得事,我只不过时间有点赶急。朱婆婆说,好好好,你今天马虎点,过两天再给我细细掏好不好?何汉晴心想,过两天哪里还能替你掏呢?过两天我都不晓得我在哪里了。想罢便说,算了,掏都掏了,还是得掏好才是。朱婆婆便笑了,说我就晓得你过细。我跟你讲,我这个耳朵也只服你掏,别个掏完了,还是痒得很,你说怪不怪。何汉晴说,我婆婆的耳朵都没有你这耳朵挑人才。朱婆婆一边揉着耳朵一边哈哈大笑了起来。朱婆婆说,你说得蛮对,你硬是个人才,一个捞耳屎的人才。何汉晴说,莫笑莫笑,小心耳朵。何汉晴掏完一只,朱婆婆用手抚着耳朵,大笑着说,真是好舒服呀。何汉晴没有笑,她对着阳光开始掏朱婆婆的第二只耳朵。才动捞耳勺,就有人大喊她的名字。何汉晴抬起头,见文三花跌跌撞撞地朝她跑来。一边跑,一边哭。何汉晴没有见文三花急成这样过,忙喊道,有么事?慢点跑。文三花跑到何汉晴跟前,腿一软,就地一坐,哭道,何姐,你要救我,你还得救我一把。何汉晴说,么事,又出了么事?文三花说,我男人被汽车撞了,还不晓得死活。何汉晴大惊,医院,跑这里来做么事?文三花说,我的伢一个人在屋里,求你帮我照应一下。何汉晴忙拉起文三花,说你这个人糊涂得也太狠了,临时不找个人看一下伢,还跑这么远来找我。文三花说,别个我又怎么放得下心。何汉晴说,多的话莫说了,医院,我立马去你屋里。文三花掏出门钥匙给何汉晴,抹着眼泪却不动脚。何汉晴说,你还不去?文三花又哭了起来,说他跟那个骚货一起出的车祸,天晓得他俩在车上做么事,开了上十年的车,怎么会一头撞到街边的树上咧?何汉晴心里怔了怔,暗骂道,这个狗男人,真不是东西。嘴上却说,还管那些,先顾了你老公的命再说。说罢,何汉晴推着文三花往前走。走了两步,何汉晴回过头对朱婆婆道,我欠你一个耳朵。说完想,这辈子算是欠下了。
15
朱婆婆摆了摆手说,莫讲这话,伢比耳朵要紧。文三花住的是楼房,那是她老公单位分的。文三花的老公在运输公司当司机,工资虽不是蛮高,但每个月的活钱不少。所以,文三花的屋里该有的东西全都有。何汉晴总说文三花的命好,文三花却说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命,不是少了这头,就是少了那头。文三花屋里虽然有点钱,可文三花老公在外面的野女人总是不断地冒出。也怪文三花太不能干,何汉晴随便几时去,她屋里从来都是一团糟。文三花的菜也做得差,结婚五六年,还做不出个团圆菜。她老公累了回来,屋里一塌糊涂不说,一口像样的热饭热菜都到不了嘴,那心思哪里能不往外野?何汉晴手把手地教文三花收拾屋子和烧菜,可到了下回去,文三花的一切都还是老样子。文三花的娘死得早,跟着一个捡垃圾的爹过日子,住的房子漏风又漏雨,饭也是三天总有两天吃不饱。活到二十几岁,嫁了人,才算把苦日子过穿。便总觉得眼前这一切都已经好得很。住的屋子夏天凉快冬天暖和,也蛮舒服,一日三餐不光有饭且还有菜。家里电视电话洗衣机,样样都齐全,就连睡床都是软软的席梦思。换了旧社会的地主资本家也过不到这样的日子。这么好了,屋里脏乱点算得了么事?不脏不乱像个豪华商场又有什么味道?还有,现在的米那么香,不要菜都能快快活活地吃下饭,配上榨菜辣萝卜小白菜,够好吃的,怎么还会咽不下去呢?文三花总也想不通这个理。何汉晴只好叹道,真是个穷坯子,教都教不会,骂也骂不醒啦。现在何汉晴站在了文三花屋里。何汉晴看到的是床上沙发上四散着大大小小的臭袜子,脏衣裤。小孩子的屎尿在地上留着醒目的印渍,桌上还落下一些吃剩的饭菜渣。屋里所有的窗子都闭得严严实实,一股污浊气,直冲鼻子。这还算好,走进厨房,何汉晴想不吓一跳都不行。地面上的油腻都结成了垢,踩上时滑溜溜的。垃圾箱的垃圾已经爆满,溢得周边到处都是。灶台边上的烂菜叶子和鱼刺估计已经放在那里两三天了,发出酸腐气。洗碗池里一堆碗,有几个碗边上的饭粒都已干硬,这也多半是好几天的饭碗没有洗。何汉晴暗骂道,像你这样过日子,莫说你男人在外头找人,我要是个男人,我还不是要到外头去找。没有休你已经是对你客气。文三花的儿子叫细伢,还睡在被子里,小脸红扑扑地,响响地吐着气。何汉晴坐在床帮,看了他一下,脑子里浮出刘最强小时候的样子。何汉晴想,未必我连儿子最后一面都不见?但如果见了,刘最强看出我要去寻死,还不鼻涕眼泪一大把地扯我的衣角,那我又怎么死得成?何汉晴这么想过,心便有些酸楚。她看了看文三花床边的电话,忍不住上前拨了刘最强手机的号码。刘最强的手机是他过生日时姑姑建美送的,虽然刘最强每个月要花不少电话费,但能够经常听到儿子的声音,而且想儿子的时候说找就能找到他,何汉晴就觉得这种钱花多少都值得。
16
刘最强一下子就接了电话。何汉晴只叫了一声强强,就哽咽无语。刘最强说,姆妈,么事,有话快说,我正在外头上网。何汉晴说,强强,你要好好的,要争气。刘最强说,姆妈你这是么样了,我不争气我考得上大学?姆妈,有么事就快说,没得事我就挂了。何汉晴好想多听听儿子的声音,可她又一时想不出什么话,于是她终于说,强强,姆妈觉得心里烦,蛮想去死。刘最强不耐烦道,姆妈,你莫没得事找事。我忙得很,你硬要去死,我未必拦得住?说这话最没得劲了。刘最强一下子把何汉晴顶得什么都说不出来。何汉晴想,你是拦不住,可是我生你养你,对你一百样迁就,你连两句留我的话劝我的话都不会说?见何汉晴没得声音,刘最强说,姆妈,没得事我挂了!说完只听得“叭”地一声,电话立即变成忙音。这声音像是从刘最强手上伸过来的一根长针,一直扎透何汉晴的心脏。何汉晴原本酸酸楚楚的心蓦地变成了难言的疼,眼泪径直就流到了面颊上。何汉晴闲不住,挽起衣袖帮文三花干活。她刚做完厨房的卫生,细伢醒了。细伢认得何汉晴,一骨碌从被窝里爬出来,说原来是老娘子来了。细伢虽只有四岁半,但小嘴惊人地会说话。有一回文三花带着细伢到何汉晴的里份里串门,路上遇到何汉晴帮隔壁杨嫁嫁剪头发。文三花就站在那里跟她们闲聊。细伢歪着头,打量何汉晴半天,说原来何伯伯是个老娘子。说得大人都笑了起来。何汉晴说,那你姆妈是么事呢?细伢说,我姆妈当然是小娘子。大人们听此言更是笑得一翻。从那以后,何汉晴就要细伢喊她“老娘子”。何汉晴见细伢光着身子爬出被窝,忙上前把他塞进去,嘴上道,慢点来,冻凉了,老娘子还赔不起你。细伢说,老娘子你跑到我屋来做么事?何汉晴说,还不是你这个小杂种要人照应。细伢说,我怎么是个小杂种呀?何汉晴说,是你爸爸和你姆妈的小杂种。细伢说,那老娘子是不是你爸爸和你姆妈的老杂种呀?何汉晴哭笑不得,在他的脸颊上拍了几个小巴掌,说你这个小杂种将来肯定不是个好东西。话说完,突然脑子里就浮出自己爸爸姆妈的样子。何汉晴的爸爸是水手,走船的时候,遇到洪水,船翻了,从此就再也不见踪影,连个尸首都没得。何汉晴的妈一辈子住在南岸嘴,汉口一发洪水,水头就会淹到屋门口。前几年整治南岸嘴,政府照顾了一套新房,何汉晴的姆妈死活都不想去住,说是住惯了小河边,上了楼,一接不到地气,二闻不到水气,这人又有么事好活头?何汉晴配合政府劝了几天,总算是搬离了。现在楼房也住得蛮舒服,说是地气接不到,可是能接到天气;水气闻不到,但能闻到雨气。天比地高,雨水比小河的水净,所以也蛮好。南岸嘴现在像个花园,前两年何汉晴去看了一回。拆了旧房子的地皮上种着麦子,绿油油一片,中间零星地杂了几棵树,一派田园风光,人走到这样的环境里,真是觉得无限养眼。对于何汉晴,南岸嘴就是她的家乡。走遍天下,总在心里。就算它改变得让人识不得,但也和何汉晴二十年的生命连在一起。何汉晴想,我死之前,还得去看一眼才是。天黑了,文三花还没有回来,连个电话都没得。何汉晴担心细伢饿,又怕文三花累死累活地回来,连口热汤都没得喝,便又扎起围裙来做饭。文三花的冰箱里几乎没有菜,何汉晴没得法,见冰箱的蛋格上还剩两个鸡蛋,只好下了一锅面条。何汉晴喂完细伢,自己也饿了,便也吃了一碗,此时业已近九点,文三花还是音讯全无。何汉晴有点急,不晓得文三花她老公到底怎么样。想打电话去问,却又不晓得往哪里打。何汉晴把文三花屋里该洗的该抹的都做了,屋里到处干干净净,明明亮亮。细伢的呵欠又打了起来,偎在何汉晴身上几分钟,就又睡了过去。放了细伢上床,何汉晴有些急,看电视又看不进,心道自己是出门寻死的,却跑到这里来替别个操心,叫刘建桥和美美晓得了,还不又笑死?又想,不晓得今晚上屋里的饭是哪个做,她没有回去,一屋的人会不会着急。要是刘建桥的脑袋会转弯,一找就找到这里来,那才是真的死不成了。何汉晴心里麻乱麻乱。十点过后,电话终于响了。是文三花的声音。文三花哭道,何姐,辛苦你了。何汉晴说,急死人的,你老公么样了?文三花说,才下手术台,命保住了。何汉晴松了一口气,说那就好,那就好。文三花还是哭,说那个狗日的骚货女人只擦破一点皮,连针都没有缝。何汉晴说,算了,人救过来了,这笔账等他好了再算。文三花说,他醒过来还叫那个骚货的名字。何姐……文三花说着说着,语不成调。何汉晴长叹一口气,说三花,你自己悠到一点。两口子的事,别个也难得说。你几时回来?文三花说,我过一下就回。细伢睡了?何汉晴说,睡得屁是屁鼾是鼾。几好个伢呀,看儿子面子,把那些事都放下算了。将来靠着伢过就是了。文三花说,何姐,老公靠不住,伢未必就靠得住?何汉晴想想觉得也是,但她不能火上加油。何汉晴说,不说这些,我挂了。何汉晴放下电话想,管不了你这些了,我要死在你前头,往后你自己顾自己吧。歪在沙发上睡着了的何汉晴突然被一阵嘈杂声惊醒,她怔忡了一下,方想起自己是在文三花的屋里。紧接着门开了,进来的是文三花。她的身后还跟了好几个人,都是乡下人打扮。何汉晴惊问:么样了?文三花说,何姐,你莫吓着了。是我婆家的两个兄弟赶过来招呼他哥的。这两个一个嫂子一个弟妹。何汉晴松下一口气,她抬头看了看钟,十二点半。何汉晴说,都吃了没有?文三花说,在外面宵了夜。何姐,辛苦你了。你要是回去嫌晚了,就在这里挤一夜。何汉晴忙说,不不不,我近得很,我这就走。文三花说,何姐,不晓得么样谢你。何汉晴想了想说,记得我就行了。文三花说,那当然记得。隔三差五地见面,哪里会不记得。何汉晴说,那也是。过些时,回南岸嘴看一看。文三花说,我早就想回去看一下的。几时我们一起去。何汉晴说,再说再说,先把你眼前的事忙下地。何汉晴说着就出了门。正是深秋,半夜里还有些寒。何汉晴只穿了薄薄的毛衣,毛衣外套了一件腈纶西装。西装的质量很一般,只穿了几个月,就四处起绒球。这是她结婚二十年时,刘建桥送给她的。为了这个,何汉晴多少对这件衣服有些偏爱,拿它做当家衣服,但凡正式一点的时候,她都只穿它。空荡荡的街上,寂寥无人,便更有寒飕飕的感觉。
精致生存与eliving一起畅享!
EforEasye从容淡定
EforExcellencee卓越正见
EforElegancee优雅自如
EforEnvisione远见卓识
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