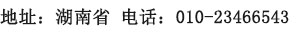文、图/李霁宇
又到河口
又到河口。
我已记不清我多少次到河口。这个边境小城给了我永远模糊时而又清晰的印象,像这里低矮的浓雾,始终流动着,波动着,这层面纱总是阴晴不定地罩在这两河之岸上,朦朦胧胧,难见它的真容。它总是闷热的,湿漉漉的,让人思绪欲滴,情愫难平。细算之下,在不同的时期我都来过河口,却无法明确地描述它,真让人惊异。这么多年我没有为河口留下一个字,也许是我的叩拜实在短暂,也许是我的心思还没有聚焦,就这样匆匆来去,只道当初是平常罢了。
其实它同我的生活有不解之缘呢。
百年前的河口城内景象年我从北京的大学毕业,一下被分配到开远。我学的专业是铁路运输,分到昆明铁路局。一报到,说昆明地区的名额没有了,你到开远地区去吧。开远在哪里?答:坐小火车去。小火车是什么火车?答曰:米轨。我这才想起教科书上讲过,还有一种轨距1米的火车。从铁路局布满法式建筑的小道穿过去便到了跑小火车的南站,站前两棵参天的大树,车站也是一栋米黄色的法式建筑,年深日久有些破败,但房基石砌,墙很厚。法式建筑都是冬暖夏凉的,初见这种建筑有些异样的感觉。站前的人多背着箩筐,甚至抱着鸡,有的蹲在阶前抱着一根粗大的竹筒吸烟,这同北京站、成都站的景象两异。我觉得我会沿着这趟年开出的火车驶向一个陌生的未来。那个时代有那个时代的流行歌,我一下想起了两首歌,一首是“从草原来到了天安门广场……”,我意识到我逆向而行,就是从天安门广场来到了某个边远的地方。另一首流行曲是:“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哪安家,祖国要我守边卡,打起背包就出发……”我那时真年轻啊,去哪里都无所谓,没有背包,手里有一个简易的小包,就义无反顾地跳上了那趟小火车。车很挤,座位是木板的,很硬,车内有一股车厢特有的臭味。多公里,车哐哐哐地开了一天,眼见天色暗下来,还没到。心想:真是越开越远了,开远就是这么来的吧?晚上车到站了,站前是一条石板铺的小街,街灯昏黄,像古时候点的小灯笼,站前街口有一座木结构的两层楼,幽暗的很大的房间,分成很多小间,那是铁路的公寓,我第一夜就住那里。门前有一个穿铁路服的老头在同人下象棋,棋子在黑黝黝的棋盘上移动,我也许是其中的一个卒,贸然地冲过了界,便只能前行,不能后退了。
这就是开远。古称阿迷州。那时叫开远县,铁路上则叫地区,是比分局还小半格的建制。但在开远,它是铁半城,占了半边天。有医院、法院、学校、俱乐部,俨然一个完整的小社会。铁路局设有机务段、工务段、车辆段、电务段、车务段。我被分到车务段,那时没有单独的客运段,客运段叫列车队,段上说:你到列车队去报到。列车队是跑开远到河口的小火车。开远成了我踏进社会的第一个人生驿站。
我从服务员、列车员干起,当过广播员、行李员、客车长甚至运转车长,多次到了河口。这小火车是米轨,这条铁路就是开河线,或称昆河线,最有名的最有历史感的名字叫做滇越铁路。当时并没有在这关乎云南历史大事件的称谓上多想——我们每天早上出发,晚上到达河口火车站,多公里要跑一整天。开远列车队是跑开远至河口的车,而开远至昆明的车由昆明客运段跑,就是说:我们只跑河口,不去昆明。
百年前两河交汇的河口那时的河口小城,城不大,人不多。从火车站辐射出去就几条小街。街上有越南人,他们显著的特点是戴一顶金字塔形的草帽,穿大脚裤,相当于多年后时兴的喇叭裤。小街上有出名的越南卷粉及各种冰镇冷饮,和味道极好的柠檬水和木瓜水,放了刨冰。当然还有硬壳的越南面包,那硬壳劲道十足,须撕咬才行,口感绵长,有类似西安泡馍的感觉,这同昆明的泡软的面包全然迥异。还有咖啡。那时的咖啡几乎是外国的代名词,觉得新奇而已。其实应该叫越南咖啡和法国面包,是舶来品,在开远也有一家这种面包店,我后来在昆明的金碧路找到一家南来盛越南咖啡面包店(以前祥云街还有一家),就是专卖硬壳面包和不放糖的咖啡。偶尔去光顾一次,不过是为了寻求一丝新意。据说硬壳面包不能用电烤箱,得用一种拱炉,先用柴火烧热,然后拆去火,再将面包放进去慢烤。河口城里的生活我们接触不多,因为跑车的关系,我们总是晚到早走,无法在小城停留。
小火车经过一天疲劳的奔波,穿过一个短短的隧道,河口火车站就到了。
铁路公寓就在车站旁边。早就汗流浃背的我们,第一件事便是冲凉。不过我们一般都不会用那简易的水管冲澡,不是因为它的水是热的,而是因为南溪河就在近侧的诱惑,于是一群青年人就三脚两步地奔向河边。一路同我们火车结伴而行的南溪河此时安静地流淌着,不再湍急,温柔似少女般平静而安谧。如果我们火车不晚点准时到达,如果我们抓紧时间下到河里,这时可以见到水面反照着夕阳橘黄色的光辉,周围全笼罩在一片金色的余晖里,那些芭蕉林宽大的叶片像风帆一样高悬,芦苇丛中依然昂扬着那些灰白色的花穗,远处高高挺拔的芒果或木瓜树会静默不动,空气总是沉着的,像在沉思默想。那些粗壮的竹林和高大的榕树作为背景,像梦幻中的布景立在丘陵和小山坡前。我们下到水里会感到另一世界的清凉,每个毛孔都渗入了无比爽快的快感。一般来说,夏天我们在车上的温度会达到摄氏40度。此刻同水亲近的这种快意无可言喻。如果我们用片石在水面上打水漂的话,那些石片会跳跃着跳过河中心——对岸就是越南。南溪河在这里就只有二三十米宽,我们可以游过去。
这里的国界正是南溪河的中心。
老铁路说:“不要游过中心就行了。”
我们试着游到河中心,然后拐个弯,出国一次,然后游回来。
对岸静悄悄。杳无人迹。
这就是上世纪60年代末的情景。
当然也有插曲。有一次一位姓邢的列车员,不知咋的,被水流冲了过去,进入了越南一边。于是大家叫喊起来。对岸有人将他救上了岸。(在中国这边,有许多沙滩浅滩,而在对岸是高岸齐岸)在越南,人家请他吃了碗米线,然后从大桥上送了回来。一时间他成了闲聊中的名人,不仅出了国,也没有引起什么国际纠纷,还被请吃了一碗米线,礼送回来。
一般来说,这段水边的时光过得很快,只十多二十分钟,天就黑了。这时南溪河岸周遭全沉入黑黝黝的夜幕中了。这时我们搅起的水花在月光下依然发出洁白的光来。那些香蕉芭蕉林全隐匿不见了,南溪河在月色下像一条镀金的银练飘动不止。我们在水草中会感到有什么鱼儿在吮吸着腿脚,痒痒的。河里有鱼吗?有多大的鱼呢?这些疑问成了我们多年后漫长回忆中的不解之谜。
河口百年前的农村从南溪河里回来,夜色沉闷,暑热依旧,不一会儿又大汗淋漓。有人就扛了床板到隧道去,这个隧道叫一号隧道,将床板架在铁轨上:睡觉。隧道本来就凉快,还有“穿堂风”呢。我们知道夜里没车。在钢轨上睡觉,令人匪夷所思。
第二天一早,这趟列车就踏上返回开远的路程。
在河口,河口火车站一带无疑是全城最繁荣的地方。至今也是这样。河口因滇越铁路而发展繁荣起来。在许多城镇,铁路都是“铁半城”。那时的开远是县,也是“铁半城”,被人们称为“火车拉来的城市”。开远城市是沿火车站一条街形成的丁字形路口,向外发展起来的。铁路沿线的小城镇更是如此,如草坝、大庄、碧色寨、芷村、南溪等。在上世纪90年代,从河口火车站出去,就是最热闹的一条起伏不平的窄小街道,全是越南人开的小商品的小店,到处是冷饮店,那种木制的压柠檬的木器简易而实用,全街充满了柠檬冰水的酸甜味儿以及树菠萝那种特殊的香臭味儿。多年后这条街已扩宽修平了,修了新建筑,几条平行的水泥街道代替了原来的简陋街边小竹屋,如今更是商店商号林立。我去寻找旧迹,却早踪迹全无了,使我惘然迷茫。时间凄美的轮回让世事沧桑,旧踪无影。
中越铁路大桥我后来在不同时期、因为不同原因又多次重返河口,除了火车站这个位置,河口的变化很大,我只有找到火车站,才能定位。火车站和河口铁路大桥是河口的标志。不过火车站不再是原来的法式建筑了,新修的火车站让我找了好一阵。这是座半球形的建筑,站前有两座高耸的灯塔,正中还有一座旗杆,挂着的五星红旗在杆顶像一团红色的火苗。如今因为滇越铁路的客运已停运了,只有货运在运行着,当年繁华热闹的火车站分外冷清,几乎杳无人迹。有一位老铁路告诉我:你看,都怪这车站修得不好。你从正面看,这车站像不像是一座坟,那两个灯塔像不像两座烛台,而那个旗杆,就是一炷香,你看,上面还有一点红红的香火呢!他这一说,我还觉得真是像。这种联想和生动的想象力在民间流传。历史的进程有时会在巧合中得到意外的诠释。我知道,那种刻骨铭心的怀念和永不消退的米轨情结,是这些民间传说最为深厚的基因。我还知道,如今在开河线沿线的所有站房站台的建筑中,那种米黄色的法式建筑多已消失,为数不多的法式建筑在寂寥中守望着过去的如金岁月。其实,在沿线的迷人风光中点缀在其间的这些黄墙红顶的建筑,曾经代表着一个时代的色彩,让我们在边陲之地接触到异国风情和外域文化,似乎昭示着一种向外开放的姿态。这最有特色的建筑群像镶嵌在历史节点上的铆钉,它将耻辱、荣光、文明和进步一块儿钉在一处,让今天的人重新思考和审视历史的这段纷繁杂陈的插页。
步出这个昔日的火车站,就是人流如织的海关,来往的边民、进出货的商家和旅游人群再现了一种今世的繁华梦境。几条商业街中商店堆积着从小电器到小百货的各种商品。在这个商圈里,早已人去物非,当年那些人已老去。那些卖柠檬汁和木瓜水的越南少女,如今在哪里呢?谁还会记得当年的景状呢?
只是当初,在上个世纪的日子里,我还没有能力并没能理解这些发展变化在人流、物流、财流大背景下的含义。一百年与一百年相遇,会有怎样的惊悸和震撼?
两河之口的叙说
河口,红河与南溪河在这里交汇而得名。
中国的入海河口众多,古代有河口记载的文献,尤其是地方志极为丰富。在湖北、吉林、浙江、哈尔滨都有河口的记载。但不是入海口而是内陆河口,作为地名的仅有云南河口这一处。
红河发源于六诏的龙兴之地巍山和大理之间,纵贯滇西南,经从巍山、南涧、新平、元江、红河、石屏、元阳、金平、个旧,从河口镇出境入越南。它流域所经大部分为云南红土地带,水色浑红,故称红河。而南溪河发源于蒙自芷村附近,于屏边、河口两县交界处大树塘流入县境。它经过的是高峡深谷、峰峦叠翠的山涧,欢快地跳荡而来,汇入红河宽阔的江流,犹如母女相会一般,红绿相依,结伴南下。这山川形胜给人一种生命的联想。两河相交注定会孕育着一种文明。这令人想起几千年前的“两河文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在两河流域的冲积平原上,他们缺乏木材和石料,用取之不尽来自两河冲积平原上的黏性泥土,制造出精美的陶器,用黏土掺上大秸秆做成砖块建筑了第一座城市,同时苏美尔人将之制成泥版,用芦苇做成的书写工具在上面刻字或画图,形成的文字符号的每一笔按压的部分痕迹宽深,拖出的部分窄浅,就像木楔一样。所以叫“楔子文字”。
展开地图,我们会看到两河相交的河口,真像楔子一样的“箭头字”,这箭头就指向南方。河口注定是一个天造地设的口岸。
中越交界全景而数千年来,河口作为一个出境口岸似乎远不如其他地区的口岸有名。为什么呢?这里固然由于它的交通不便,古代的南方陆上丝绸之路并不向河口一线集中。大约是20多年前,我从成都南下考察南方丝绸之路,经新津、邛崃的“临邛道”,芦山、萦经、汉源的“青衣道”,进入“牦牛道”的雅安、石棉、冤宁、西昌、会理、攀枝花,从宁蒗就进入云南的丽江、剑川、大理,再经巍山、永平到保山,从保山入缅。南方丝绸之路往东的一条是从四川宜宾进入昭通,这就是有名的“五尺道”。公元前年,秦派李冰——就是那位因修筑都江堰而造福万民、遗荫千秋的蜀郡太守,开始在僰道(今宜宾)的崇山峻岭中开山凿岩,修筑通往朱提(今昭通)的驿道。到汉武帝时,又开始了对这条道路的续修,五尺道于公元前年全部完工,从僰道经朱提(今昭通),达建宁(今曲靖),史称秦汉之际,川滇之间“栈道千里,无所不通”。茶马古道中的滇——藏路线是:西双版纳、普洱、大理、丽江、德钦,再到拉萨。另一条从四川雅安出发,经泸定、康定、昌都再到西藏。然后进入印度。而进入越南,多是从广西进入的。
这里恐怕还涉及历史。
这就是越南的历史。越南古称交趾。交趾是西汉所建立的一郡,包括越南北部及广西南部的一部分土地。“交趾”一词,最早出自《韩非子》。其文曰:“尧帝之地,南至交趾。”上古时代,在今天湘、粤交界处一带的人们因为有“卧时头向外、足在内而相交”的习惯,因此才称之为交趾。古书上有好几种解释:有的说,那地方的人睡觉时头部向外而足在内互相交叉;有的说,他们的大足趾叉得很开,双足并立时两个足趾相交;另有一说是趾即址字,汉武帝北置朔方,南置交址,是“交”为子孙福“址”的意思。西汉时,元鼎六年(前年)汉平南越国,在原南越王国地方设交趾郡,后改名交州。三国时期,东吴将南岭以南诸郡以今天广西北海市合浦为界,以北广州,以南为交州。交州共设有三郡(交趾、九真、日南)五十六县。
我对交趾的认识是从年轻时读《红楼梦》中来的。《红楼梦》中五十一回里有薛宝琴新编怀古诗十首,内隐十物。其中一首是《交趾怀古》:“铜铸金镛振纪纲,声传海外播戎羌,马援自是功劳大,铁笛无烦说子房。”这才知道马援称伏波将军,平交趾征姓二女有功,同时知道交趾就是今天的越南。谜底呢,一说是叹荣宁勋业为马伏波,暗藏河图;又交趾何事,隐云雨情,隐垢象。二说是扬琴,琴之作用书如观海。还有一说,似是马上招军的喇叭。另有人说谜底是自鸣钟,是象棋的。至于谜底真假,姑且不论。至于交趾所解,查无据。今天越南人肯定不是这样,要是这样,这里所说的也是湘、粤交界处一带的中国人。这湖广人进入越南看来是古已有之的传统。到了近现代,广西人入越南的很多,有的入了越南籍,有的成了华侨。
古时河口作为出海外的通道,它自然不敌其他通道。换言之,那时的物流也只是境内交易而已。那时交趾一直向中国朝贡。年,明朝承认大越黎氏政权越南,从此越南独立至今。年12月至年4月(光绪九年十一月至十一年二月),由于法国侵略越南并进而侵略中国而引起的中法战争,签订中法条约,彻底割断了中越之间曾经的藩属关系,河口作为出境的口岸的声名长期被掩蔽了。
边民互市交易市场从内地进入云南,有民谚称:“一天上一丈,云南在天上。”
云南是高原,云南最高海拔米,昆明海拔米,最低海拔76.4米,这最低海拔76.4米的地方就是:河口。同进入云南相反,从云南的南部出境,云南就从天上回到人间。就地势而言,两河之口的河口,像一个喇叭呼唤着一个声音:向南,向南!这声音亘古不变,千年不绝。早在19世纪末,法国人以“云南考察报告”为蓝本的《云南铁路(译本)》提出了最为经典的论断:“云南真正的出海口并不在东方,即广东和香港方向,而是在东南方直接由红河山谷通向海防和东京湾(今北部湾)的方向……”
万壑归流,从河口入海成了必然。红河在河口县境内92.6公里,坡降7.9%,至河口新街一段9公里为中越两国界河,坡降22.5%。水流带来的物流也是必然。古代云南与内地联系的通道,主要有三个方向:一是向四川,一是朝两广,再就是向湖南。在许多人的印象中,马帮是高原运输业中的主角,茶马古道是沟通省内外的主要交通线,却不知云南自古就有通向沿海,直奔大海的“黄金水道”。同样,在许多人的印象中,这条水道是从水路至横山,下邕州(今南宁),运往两广等沿海地区。云南山高峡深,独龙江、大盈江、瑞丽江(伊洛瓦底江的三大支流)、怒江(萨尔温江)、澜沧江(及其下游湄公河)与红河则由西向南,分别经老挝、缅甸、泰国、柬埔寨、越南五国后流入印度洋和太平洋,但在境内蜿蜒奔流的这些大江大河水流湍急而不通舟楫,唯有红河经过长途跋涉,在进入下游时河岸宽阔,水流趋于平缓——这就是从河口出境,经越南河内、海防、北部湾入海的另一条“黄金水道”。这条水道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了。
这也就是两河之口的天籁之声。
南溪河畔的鹅卵石
我站在南溪河畔,眺望远处平静流淌的河面,追踪记忆里的岁月,我一直以为她是跳跃的、欢快的、不安分的,因为她年轻,像刚刚出山的村姑,面对世界还保留着那份纯真和单纯,她也许生过气,赌气将那朵朵白色的花朵掷在精雕细刻的山壁上,绽放开清纯的氤氲香气,她也许高兴了,就三脚两步地跳下悬崖,淘气地躲藏在岩层中,偶尔吐出一圈涟漪,招呼捉迷藏的伙伴,她也许还真发过怒,放荡不羁地狂奔,听不进任何劝阻……如今,她累了,小憩片刻,安安静静地睡了。——她不知道她是迷人的。
我记忆中她是从峰峦叠嶂的幽谷出来的。像一个美丽的精灵。
这里是一片沙滩,静谧而安详。河岸上是成群的芭蕉林,一棵巨大的参天榕树伸出华盖,伞一样地留下半亩地的绿荫。那粗厚宽阔的气根光滑浑圆像一件鬼斧神工的工艺品。这片半月形的沙滩仿佛就是这树荫光明的影子。南溪河在这里轻轻地转了一下身子。这沙滩上的沙砾和小小的鹅卵石像珍珠一样铺展在这半钩月轮上。远处轻曼无声的绿水漫过来,像有人轻轻抖动的绸缎,展示那无与伦比的花纹和波光。上游不远处是嵯岈的崖石切断了这匹锦缎,在月儿的尖端处挑起了一丛丛郁郁葱葱的花枝。河滩上的石块都是圆形的,不大,适中,最多的是像汤圆般大的鹅卵石,星星点点地散落在这里。最有趣的是,好多鹅卵石是扁的,就是说它是薄薄的,甚至只半厘米厚,边沿光洁而光滑,这在其他各处很少见,有的竟像是一枚枚圆币。那些弧形很圆,像标准制造似的。大自然用光阴打磨了这些精致小巧的石块,表达了岁月无尽的心事。我想,这是南溪河有意留下的心跳。
我弓着腰,在沙滩上寻找拾掇这些遗失的时光。
这些时光是斑斓的。
那些石头有的呈黑灰色,有的是纯白色,还有的是棕红色,多数为杂色相间,色块奇形怪状。我虽没有徐霞客嗜石之癖,但我也曾经收藏过雨花石,那种石头名气很大。我曾经喜爱过大理石,因为它的花纹总出其不意地激发你的想象。我也曾珍藏过大漠奇石和大海怪石,图的是个新奇。记忆中,我为香溪的昭君石写过散文,也为丝路古道上的花岗石写过文章,我还为泰山的极顶石写过诗。还有名不见经传的金沙江石,但那些石子都比较大。
这里的石头都不大。
我知道,这是一条河流下游中的石头。我曾经到过甘肃、湖北深山里一些河流的上游,那些巨石有的如方桌大,甚至有的如房子大,耸立在水流中。人们过河可以从一块块大石上跳过去。那些石头全是方方正正的,或者全是有棱角的,多面体的,锋芒毕露。经过了时间和水的打磨,多少年了,多少路程啊,它们终于失去了棱角,渐渐变得光滑和圆熟了。也开始变小,最终成了一个个沙滩上的鹅卵石。世界上年龄最大的是石头。它的古老让人类都成了年轻的后生。眼前这一块块小石头,它起码有上亿年的历史。始信,石中有万古苍寰,石中有六合乾坤。一想起这方石头的所见所闻所经历的沧桑,就不由不让人震撼,并感到它沉重的分量。
通向越南老街的铁路南溪河的石子并不出名,只因它还藏在深闺,其实,它的美丽并不亚于那些声名远播的雨花石。
这时,平静的河滩上响起了笑声。一群十三四岁的孩子们嬉戏着来到河滩,不知是课余还是假日,他们一群来到这里,在河滩上架起枯枝,拢起火来。火很小,半是火苗半是烟。他们烤着带来的小食品。男孩子穿着红色的小三角裤就扑向河里。女孩子守着火堆在吃零食。有两个孩子还推来了两辆山地自行车。在沙滩上,他们骑着车冲向河里,一阵叽叽喳喳的声音后车就冲到水里,马上就翻车了,人一下掉下水,众孩子就高声叫着闹着。有的孩子干脆穿着衣服在水里打闹,全然不顾一身湿淋淋的。他们打闹着,在水边溅起无拘无束的浪花。
这段南溪河靠近山腰一带。流过这里,拐一个弯,就到了河口了。河对岸就是越南。那里的河岸高些,没有这边的浅滩沙渚。高岸上似乎有路,不时有一辆辆摩托车飞驰而过,只见那车影很快就消失在岸上绿荫丛中。
他们有时会对着对岸一闪而过的摩托车挥手叫喊着。
他们清楚曾经有过的绵长悠远的历史和那段起伏不定的时局吗?他们清楚这千回百转来到这里的流水有过怎样的坎坷和波折吗?他们那么年轻,而那棵老榕树却无言地注视着这个场景,这种宽容和理解意味着什么呢?
叔叔,你在捡石头吗?
看我手上一摞像钱币一样的石片,他们也不约而同地捡了起来。
如果这石块大一些的话,就可以回到童年游戏:打水漂。果然几个孩子就拿起挑拣的圆石块打起水漂来。那些美丽的圆圆的石片就飞向水面,优雅地沿着水面漂去,点画出一圈圈水波,圈子渐次变小变密,而石块就消失在水下了。这时,它已经过境,到了越南一方了。一水相依,一水相隔,一水为界,一水相连。山连水,水连水,就是这样来的。两岸的植被同样的郁郁葱葱,依然是香蕉林和常绿的阔叶林,草丛和葛藤,芦苇和野花。一条爬坡上坎、九曲回肠的流水和一段是非反复的历史长河就这样交织在一起,让人萌动一波三折的思绪,在时空的交错中骚动不宁。
“叔叔,你要捡好看的石头吗?”又一个童音在耳旁响起。
不待我答话。他说:“我知道那边有一个好看的石头。”
他说着就向水边走去。前方水流中有一片突起的沙洲,宛如一个低矮的小岛,水从它那里分流而下,再汇合流来。他赤足涉水过去,水很浅,他到了那片小沙渚上低头在寻找。
不一会儿他过来了,手里拿着一块石头。
我接过来,这是一块手掌大的扁平圆圆的石头。通体褐黑色,但石中有花白的小斑点和棕红色清晰细细的纹路。古人云:品石有道,爱石凭心,敬石缘性,认石因人。我点点头说:“好!这是一块漂亮的石头。”孩子得意地笑笑,找他的同伴去了。那孩子走后,我仔细端详这块美丽的石头,蓦地发现,那些棕红色的细纹,好像是构成了一个字——一横和一竖构成一个直角,在这个空间里有一个方方的口字纹路。旁边是无数的小白点。白点是水,这纹路仿如一个可字,加起来,这不是一个“河”字吗?
啊,河口!
南溪河奔来河口,用它的生命镌刻上这个天意的铭记。我感应到了。
于是,我抚摸那块石头,遥想亿万年的造化和历史的纷扰,并倾听今天的回响。我真的听到了。
古道秘踪
我在云南这片土地上漫游,去过大部分的州县,也就见过无数的古道。有的是古丝路,有的是茶马古道,有的是民间便道。根据我的经验和见识,我已不能分清哪些是丝路哪些是茶马古道哪些是官道哪些是民间便道了。这些古道多半隐藏在大路或现代公路之侧,有的还潜伏很远很远,久已荒芜,罕有足迹了。有时,试着走进去一小段,渐入蛮荒或丛林,不知去向,云深不知处,便只好打道回府了。
从南溪河溯流而上,我们不时可以见到横跨南溪河的若干吊桥。有的较宽,铁索,木板,显然是近代所建,有的窄一些,走在上面置于江风冽冽中,桥面晃荡很厉害,桥下滚滚急流令人晕眩。更有些仅能容一人通过,细细的绳索和铁丝呈半朽状,铺的木板残缺不全,更令人胆战心惊,有的可能也多年不用了,人都不敢上去一试胆量。这些大大小小的吊桥从岸边树丛中伸出,像同自然开的玩笑,远看如一些火柴棍搭成的玩具。退回去若干年,它们更多是用木竹搭成,通向山峦背后的那些边远的村寨。这些民间的通道连接着无数的崎岖山路和羊肠小道,形成了密如蛛网的小通道,再接上那些古道上的干道和支线,便形成了更大的交通网。生活用品在这里流通交换,但它还远远算不上商道。
如果我们从这些年代久远的吊桥走下去,我们会看到或体会到什么呢?我曾经看过一个纪录片,是记述非洲一处大河上的吊桥。这大河足足有上百米宽,洪流咆哮如雷,浩浩荡荡,而当地土人竟然可以在上面搭了吊桥,而且没有金属和工具,他们只有当地的野草!这草约一市尺多长,他们用这一尺长的草错开编织成手指粗的草绳,然后再用这种手指粗的草绳三股合在一起再进行编织成手臂粗的草绳,再用这种草绳反复多次编织成大碗口粗的草绳,他们竟然用这种草绳拉起了米宽的吊桥,真让人惊诧不已!古人的智慧和坚韧竟创造了难以想象的奇迹。这些土石小道也是千百年用脚踩出来的奇迹,是最初商品交换的雏形。云南著名的社会学家方国瑜先生说:“甲部落与乙部落之间有通道,乙部落与丙部落之间有通道,丙与丁,丁与……之间亦有通道,递相联络,而成为长距离之交通线。此交通线以滇池为中心,往西经昆明、雟唐、越嶲、敦忍乙,以达曼尼坡而入天竺;往北经西僰或邛都抵于蜀以达秦;往东经夜郎、牂牁抵于巴,以达于楚。再由秦、楚通于中原及江南各地,以交通线为大动脉,西南各部族与内地相联系。西南各部族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并非孤立,是中国整体之一部分。自有历史以来如此,唯在程度上,古初稀疏,后渐频繁加密。数千年历史发展过程如此也。”对于近代民间小道的考察似乎缺失,至今没有一份完整的记录,就更别说古代的了。
中越铁路大桥对于古道干线的考察和记述很多。不能尽述。
古代丝绸之路南北丝路我都去过,南方丝绸之路的东西两条线我也都去过,那些五尺道上的蹄印、驿道关隘的险峻、悬空的栈道,紧贴山壁开出的明道,有多文记述。而云南南部的红河、文山等地古有通往交趾(越南)的道路,由河口出境,到达出海口仅四五百公里,是云南最近的出海路线,实际也就是古代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的某些支线。茶马古道是特指唐宋以来“茶马互市”的古道,这样的话,同古代丝绸之路相差约几百年到一千年。干线、支线和小道在地理和时段上多有交叉、重叠,然而这些分岔的古道的记述多为零散,总体的记述却不多。在这些崎岖难行的交通线上,多数还是人背马驮的,它同那些官道或者军道有区别,因此云南的“山间铃响马帮来”就成了云南的绝唱。
马帮是云南独特的风景。它的历史应在古代丝路之前,不过北方丝绸之路是骆驼,南方丝绸之路是马或骡。它是以民间交往、自发贸易的方式逐渐形成道路并交通的,并且始终以民间运输力量、民生民用物资为主体。远古的详情已经不可考证,到了唐宋时期才有了些记载和资料。茶马互市起源于唐宋时期。那时战乱频仍,需要战马,马便成了茶马道上大宗交易品,茶马贸易,出卖茶叶,购买战马。宋朝在四川设置茶马司,将四川的年产的万斤茶叶大部分运往甘肃、青海地区,设置了数以百计的卖茶场和数十个买马场,并规定只许买马不得它用,每年买马达匹以上。从而使青藏道既是军事政治要道也是贸易往来的商道。据说藏区和川、滇边地则产良马。川马或滇马都比较矮小,它们走山路爬坡上坎肯定是良驹,但作为战马是否合适,我一直存疑。然而民间役使和军队征战,都需要大量的骡马。所以这“马”,可能并非专指是呼啸沙场的战马。西北的汗血马或如“马踏飞燕”中的神马,似乎不产于西南吧?明代文学家汤显祖在《茶马》诗中这样写道:“黑茶一何美,羌马一何殊。”“羌马与黄茶,胡马求金珠。”说的羌马和胡马大约不会是川滇藏的马吧?所以我以为这马的交易,可能渐渐式微,可能交换的是另一些货物,比如盐茶、布匹、糖和香烟等。当然还是以茶为主,所以有时人们将这古道称为“茶道”。事实上,到清朝,茶马治边政策有所松弛,私茶商人较多,在茶马交易中则费茶多而获马少。至清朝雍正十三年(年),官营茶马交易制度彻底终止。然而这条道依然为民间所用,马帮依然络绎不绝,马夫们酸甜苦辣的风情故事,和那边走边唱的马铃声,依旧荡漾着唐风宋魂的刀剑与柔情。
虽然马不再作为军马、战马,但在滇云古道上驮物仍以滇马为运输工具。据内行介绍,滇马个子不大,“云南十八怪——袖珍滇马跑得快……”矮种的滇马皮毛大多黑中带红,毛色光滑闪亮,在鼻梁、腿部多杂有花斑。它们体形虽小,但是耐力且耐驮。滇马细分有马与骡之别,骡又优于马。骡子四蹄只要稳稳地一踩下去,那铁蹄精准得离悬崖深涧只差毫厘,步调灵活,耐力特好,善跋山涉水,能忍饥耐渴,适应温差变化,性情又温和。山区路窄坡陡,有些地方骡更具优势。一则骡的负荷力强,壮年骡子可驮二百斤以上,马能负重百十斤左右。
对那些马帮不愿承运的量小且路途短的货物,就要靠人力了——这就是背夫求之不得的活计。背夫负重运货全凭一己之力,更比赶马人苦命得多。他们上路少则三五成群,多则一二十人结队。轻者日行40里,重者日行二三十里。背夫肩上架有一块中央呈半圆缺口(脖子可伸出),像枷一样的木板,背负一竹篾编制的高背箩,装上百十来斤货,手持一根上面有块长尺许,宽约半尺的半月形木板,像个独脚凳的工具,行走时做拄杖,途中暂息,背子不卸肩,用丁字形杵拐支撑背子歇气。杵头为铁制,每杵必放在硬石块上,天长日久,石上也就留下窝痕。他们腰间系有一篾片,用来刮汗水,别上根烟锅,挂上几双扎实的草鞋、水囊或装水竹筒、自带干粮就上路了。路程多在县际之间,有时也穿越数县,如把黑井的盐背到思茅,把普洱的茶背到昆明。他们闲时务工,农忙时回村务农。同马帮比,算是业余的吧?
古道上深深浅浅的印迹,到底是马蹄印呢,还是这杵头印?或者是两者相加。这个问题没有人能解惑。
茶始终为茶马古道上的大宗货物是肯定的。康藏属高寒地区,海拔都在三四千米以上,糌粑、奶类、酥油、牛羊肉是藏民的主食。在高寒地区,需要摄入含热量高的脂肪,但没有蔬菜,糌粑又燥热,过多的脂肪在人体内不易分解,而茶叶既能够分解脂肪,又防止燥热,故藏民在长期的生活中,创造了喝酥油茶的高原生活习惯。肉食乳饮的畜牧人民皆饮茶成风。西北各族纷纷在沿边卖马以购买茶叶。但那些地区不产茶,只有从这古道上运进茶叶。茶便如盐一样金贵。在中国,古代有几样东西是对外国人保密的,一是丝绸,二是造纸,三就是茶了。以前在陆上丝路即北方丝绸之路上是有海关的,严防蚕茧桑种出口。海关就是嘉峪关、玉门关等。而茶叶,也是一桩秘密。在法国某个收藏家家中,保存了一套家藏的中国水彩画系列,其中就画有制造茶叶的全套工艺:它描绘茶叶生长在悬岩峭壁上,人们训练猴子去采茶,然后,人们在另一地方宰杀野马,用野马的体液冲茶,于是茶才茶香四溢。这个极具想象力的谎言也许真的蒙骗了西方好几世纪。古代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就这样在保密和泄密中冲决了种种壁垒,发展起来。在西南的茶马古道上,可能也演绎了这个十分漫长的过程,最终让茶叶成为了出口的拳头产品。——其实我一直有些奇怪,这老外咋就学不会种茶?
当年通过古道出口的茶叫大叶茶。也就是今天人们所说的普洱茶。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家乡成都时,有远亲就从藏区带来沱茶,模样就像北方所吃的窝窝头。那其实就是普洱茶,是马帮长年驮在路上用的下等茶,远不像今天炒作的那样名贵。民国年间滇茶除销本省外,以销川、康、藏为大宗,间销安南、暹罗、缅甸及我国沿海沿江各省,它们大多依赖骡马,而走水道或者火车者不多。我以为,那些大叶茶都是长年累月在马背上自然发酵而成了熟茶,成就了普洱的特色。比如从昌都到雅安,光是骑马就得走四十五天。从雅安经昌都至拉萨的交通,全靠驿道和牦牛,每天行走三四十里路,来回一趟要费时一年,由于受季节的限制,一年中能真正通行的只有四五个月时间。从云南普洱茶原产地(今西双版纳、思茅等地)出发,经大理到西藏,然后再经江孜、亚东,分别到缅甸、尼泊尔、印度,仅国内路线全长多公里。因此,我甚至认为在马背上发酵的普洱熟茶才是正宗的呢!——因为马与茶终于相映成趣、相得益彰,真正完成了茶马古道完整的诠释!
请看埃德加·斯诺在年底跟随马帮在盐茶马道的记述:“……这个马帮有六十匹腾越骡子和健壮的小型马。它们驮着棉花、鸦片,另外有两三驮玉石或琥珀……这个马帮特别兴旺,连马锅头都骑马,这是很少见的。他骑一匹精力旺盛的小马驹,纯黑色,颈项上套着一圈铃铛,欢快地响个不停。他的坐垫是一块美丽的西藏毛毯,他骑在马上胳膊向外伸开,这是典型的云南姿势。他的双肩上,一边挂着黄色丝巾,另一边挂着一长串银珠子,腰间挂一把银剑。还有头上,老天爷,他头上才叫好看,他头戴一顶软皮帽,帽檐上插着一根雉鸡毛,好一副豪侠气概!他从我旁边走过,笑着向我打招呼,露出了洁白的牙齿。他知道,他是多么英俊,多么富丽堂皇。我像看见了罗宾汉似的,大为神往。”(原载年9月1日纽约《太阳报》)
山高,不有我的脚螺蛳高;
山矮,不有我的磕稀头(儿)矮……
——这意味深长的赶马调,将世界变为一个活着的寓言,变为一个千年的倒影,变为一个万古不变的生命誓言。它穿越时空在高不见顶、低不见底的峡谷中盘旋。直到今天仍感人心魄。
蜿蜒的滇越铁路伸向越南境内茶马古道中的滇、藏路线是:经西双版纳、普洱、大理、丽江、德钦,再到拉萨。另一条从四川雅安出发,经泸定、康定、昌都再到西藏。据李晓先生的记述,马帮走东北边昭通一带,路绕羊肠,曲曲拐拐不知多少弯,步步绕山转。上至半山,气候即冷,须加衣数件,方可御寒。要是在冬季还要穿上棉袄、毛皮褂,不然则寒冷难耐。愈近山顶,天气愈加阴寒,细雨蒙蒙,云雾迷茫。下山路泥泞石滑,人马难行,四季如此。自古有“四十八拐上梨山”和“六十八拐下大关”,更有一处“九十余拐到山巅”之谚。马帮北行武定、元谋、金沙江,路上怪石奇树遍布,山茅野草高过人。春夏之时,蛇蝎出没于石罅间,大蛇及丈,小也长二三尺,或横卧,或盘踞于路径,见人就窜入草丛。蝎子大若尺许,见人即作战斗状。蚂蚁则遍地都是,色红而透明,如琥珀琢成,行走迅疾。山蚂蟥长二三寸,能飞附人身吮血。有人见过尺长的蜈蚣,在夜雨中闪闪发光,同雷雨相映,让人触目惊心。“山顶似冰窖,山脚像火塘”。马帮走西北丽江、中甸一路进藏,越走海拔越高,天气越寒冷,空气越稀薄。通常夏季进藏到拉萨或康定,入秋就回来。如果时间把握不好,冬天大雪封山就不能通行。这一条路沿线人烟极稀少,无马店,要自备更多的口粮给养,衣物要多,帐篷要厚,甚至带上干柴、干牛粪饼,用做燃料,比走其他方向的马帮更艰苦。如远去印度,就先一直向北到拉萨,则一年一个单边。
而走南边呢?瘴气袭人,蚊蝇毒虫、蛇蝎蚂蟥,遍布丛林沟壑。此路古称“蜀身毒道”,身毒(今印度)虽是古代译名,但古人如此译法显然是有其深意的,仅以此汉字的表面意思,可知此路之险。加上雨水多,水流湍急,遇到雨季,河水上涨,须趟水过河。马帮趟水过河并非小事,得由经验丰富的锅头选择渡口,测定水流缓急深浅,估计趟水过河需多少时间,趟水过程中会不会发生大雨和山洪。稍有失误,全帮趟不过河,有时趟到河心,被困在沙滩上,或连人带马全部被山洪冲走,尸骨不存。
南边就是往东南亚。
印度史书《政事论》和《摩奴法典》就记载,早在公元前四世纪时,四川的丝和丝绸就已远销到印度,并通过印度转销到西亚、非洲和欧洲。南诏、大理国时,与印度的大秦婆罗门国(今印度阿萨姆邦)、缅甸北部的寻传、大赕,中部、南部的骠国、弥臣、弥诺,孟加拉国的小婆罗门国(今吉大港附近),以及交趾(越南)、真腊(柬埔寨)、暹罗(泰国)、老挝均有贸易往来。宋时,缅甸已有中国生丝织成的缅甸纱笼。明代时,缅甸的宝石、玉石大量输入中国,云南的对外贸易也由贵重商品扩大到民间日用品。年后,云南的蒙自、腾越(腾冲)、思茅先后开辟为商埠,设立了海关,拥有了对缅甸、越南等国进出口贸易的优惠条件,于是对东南亚诸国的进出口货物剧增,连带马帮运输业务进一步繁荣起来。
到河口、越南就得辗转先到蒙自,再到蛮耗,经水路溯红河到河内。也可以从陆路到老挝,再由老挝琅勃拉邦到越南。通过这条古道,在明朝,玉米由此传入中国,而越南的占城稻米也由此进入。这条古道到了清代,进出口货物品种和规模进一步扩大,与越南、老挝的贸易有很大的发展,茶叶、漆、安息香、瓷器和棉织品成为主要的进出口商品,直接促进了云南矿业、手工业的迅猛增长。
而马匹就在这条道上老去,历史和人也老去。
今天,我们思绪万千地站在空寂无人的古道上,极目远望,越过逶迤穿越时空的古道,意识到历史如古道一样的悠长而无尽头。
帆影绰绰
江河似乎是古代最重要的交通通道。在没有现代交通工具汽车、火车、飞机之前,几千年的史书和文献上出现最多的字是:帆。唐诗宋词元曲上的这个“帆”字,比比皆是,数不胜数。人不能负重远行,滑竿或轿子更差,马帮的行程极其缓慢,当然可以骑马,然而以快马传书、日行八百的速度,只有为杨贵妃送荔枝的特例了。人众且货多的情况下,唯有船帆能胜任。直济云帆的豪情和孤帆远影的诗意就这样交织和渗透进中国的文化中,我甚至以为,没有江河的帆影,中国不可能有那么多诗意的文字并成为诗国。
船舟天生就是自由和浪漫的象征。商人或者官宦、文人、游子,在船上可以歇息而不必操劳和劳累,沿岸的大自然必然壮美或绝美,这是蜗居市井无法得到的且是千变万化的别样风景。于是被自然和幻想哺育,就有了那么多的诗情画意,留下了那么多华美的篇章和传颂千古的诗歌。
那些乘船到越南的行旅中,商贾们似乎心无旁骛,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诗文记载。到了公元7世纪的一天,诗人杜审言写了首诗《旅寓安南》。这杜审言何以到了安南(越南),详情不知,但可见当时已有官员或士大夫因缘到了这边远之地。杜审言是何人,多数人不清楚,他原来是大诗人杜甫的祖父!他这首诗倒把越南的风景和气候写得恰如其分了:
交趾殊风候,寒迟暖复催。仲冬山果熟,正月野花开。积雨生昏雾,轻霜下震雷。故乡逾万里,客思倍从来。
有意思的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也与交趾有关。王勃的名篇《滕王阁序》名世,其“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成了千古名句。上元二年(年)或三年(年)春天,王勃从龙门老家南下,一路经洛阳、扬州、江宁,九月初到了洪州。在这里王勃留下了《滕王阁序》这一传世名篇。滕王阁大宴后,王勃继续南下,于十一月初七到达岭南都督府所在地南海,第二年秋由广州渡海赴交趾,不幸溺水而卒,年仅二十七岁。他去交趾干什么呢?去看望父亲,而他父亲就在交趾!
可见交趾在古代已同内地有许多往来,而这种往来必定是建立在通商贸易的基础之上的。不然,这位王勃的老父和杜甫的祖父千里迢迢到交趾,总不会是旅游吧?我猜想他们多有一官半职或有公务在身。
我们今天站在河口的红河边,已经见不到船楫风帆了。红河浑厚无言地流过,有点沉默。在它怀里演绎过的壮阔图景跟流水般的历史远去了。再也不见云帆直挂济沧海的壮丽景象了。
其实当初的码头并不在河口的大桥这里。而是在它的上游,近百公里外的地方,那里叫蛮耗。这是一个曾经响当当的名字。
蛮耗是今天个旧市境内的一个镇,地处金平、个旧、屏边、蒙自的节点上,在公里的滇越古道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在滇越铁路通车以前,几千年来都是红河上的重要港口,不少物资经蛮耗装船顺红河而下,经河口进入越南出境;进省物资也循此运到蛮耗,再转运省内各地,故曾兴旺热闹非凡。
这条航道古已有之,不过那都是小量或短途的运输,大宗的运输并正式成为跨境商道已是19世纪了。年,法国海军组织了一支探索队,走遍了湄公河,最后通过红河抵达了中国的大理,终于发现红河可以成为越南进入中国南部的通道。这一发现,由探险队员安邺撰文发表在《两世界》等杂志上,安邺很快成了欧洲著名的地理探险家。以前通常的贸易路线是由海上将货运到上海等通商口岸,再由陆路运到云南。这条商路过于遥远。红河通道的这次探险吸引了法国军火商人堵布益的注意。他说动了法国海军部,到了年10月,堵布益招募了23名法国人,45名马来人和80名中国人组成的雇佣军,购买了两艘英国海军的“青花鱼”级炮舰——“甲虫”和“商行”,分别更名为“红河”和“老街”,并与“山西”号轮船和一艘帆船组成舰队。在10月,满载泰来洋行的军火等物资的舰队,从海防进入红河进入云南,于2月底到达河口。3月4日到达蛮耗,弃船步行12天抵昆明。4月29日离开昆明,再沿红河顺流而下。——因为这个行动,法国还与越南地方政府发生了一次战争,最后签署了一个《西贡条约》,法国人要求越南开放红河,并允许法国在河内、海防(中越两国称其地为左金,海防是法国人的叫法)设立领事馆及驻兵,但最终只在河内一个城市获得了经商权。直到年8月25日,越南被迫签订了《顺化条约》,法国才取得了对越南的“保护权”。顺带说一句,那位最早参加探险的安邺,已是上尉的他作为法国的特遣队队长,在这次战争中被黑旗军砍了脑袋。而商人堵布益却发了大财。——历史人物就这样不经意间完成了历史使命,完成了历史的意外结局。
经此之后,红河的航道算是正式开通了。
清朝中叶,蒙自逐渐成为滇越水陆通道的要冲。咸丰、同治年间,大批的广东人从惠州、潮州、韶州等地历尽千难万险来到蒙自所属的蛮耗,在荒凉的红河边上辟地建房,把偏僻的蛮耗古渡口建成水陆转运埠头。内地及海外货物可以先在越南海防中转,然后经越南老街沿红河水道运至蛮耗驳岸,再用马驮陆运58公里到蒙自集散,最后北运昆明,西运普洱,东运开化(今文山)。尽管红河水道滩多流急,河中暗礁广布,两岸山势险峻,河谷中瘴疠逼人,到雨季河水暴涨更是危机四伏,沉船事故时有发生。但是,在滇越铁路通车以前,由越南进入云南内地,这条水道最为便捷,它是清末民初云南外贸的最主要的通道。当时货运马帮由昆明经通海、建水至蒙自计9个日程,蒙自至蛮耗2个日程,由蛮耗顺流而下航行至越南海防20个日程,从海防港换乘轮船4天即可到达世界著名的自由贸易港——香港。从个旧经蒙自关出口大锡,走这条捷径只需27个日程就能抵达香港。
据道光《云南志钞》卷6《边裔志下?越南载记》:云南入交趾有二道:其一道由蒙自经莲花滩(今河口新街处)入交州之石陇关,下程澜峒,循洮江(红河古称)源右岸四日至水尾州,又八日至交盘州,又五日至镇安县,又五日至夏华县,又二日至清波县,又三日至临洮府洮水……临洮三日至山围县,又二日至兴化府……自兴化一日至白鹤神庙三歧江,又四日至白鹤县,渡富良江;其一道自河阳隘循洮江左岸,十日至平源州,又五日至福安县,又一日至宣江州,又二日至端雄府,又五日至白鹤三歧江,然皆山径,欹侧难行;其循洮江右岸入者,地势平夷,乃大道也;由莲花滩达安南之东都,可五日而至。
束世澂《中法外交史》引《越事备考》中载:“滇南所产铜、铅、铁、锡、鸦片烟,取道红河出洋。各项洋货又取道红河入滇,愈行愈熟,已成通衙。”年《光绪十五年北海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中载:“光绪十年以前,安南未成法国属地之时,所有洋货运往云南省属之南及广西属之西,皆系经海防而去,运到老街、浪顺、芒街等处。”由此可知,在中法战争爆发前,个旧所产锡块即已由该商路外销。
蒙自开关时,红河航道最大的问题是自老街起至蛮耗的适航性差,红河水道狭窄迂回,河床落差大,水流湍急,多有暗礁险滩,在由老街到蛮耗的华里的航程中,便有大小滩多处,其中险滩有犬滩、莲花滩、新滩、乌龟滩等11处之多,商船往往需结队而行,尤其是逆水上行时,若遇过滩时,通常需要不少人集中力量拉纤,将船只一一拉过滩。此外,每年5~9月份这一区处于雨季,在持续的强降雨影响下,通常山洪暴发,河水位猛涨,流速极快,传统的舢板小船根本无法行驶,使得红河水路运输具有季节性的特点。这些都给贸易带来了不小影响。
红河水道对于多山的云南省,其商贸意义不言而喻。根据蒙自海关年贸易报告册所载,从海防至河内由轮船运行,历时1天;从河内至老街由帆船运行,历时20天;从老街至蛮耗亦用帆船,需时7天;从蛮耗至蒙自陆路运输由驮畜完成,需要3天;蒙自到云南府城也由驮畜完成,需要9天。从海防至昆明全程需要40天的时间。从此出现了“大船三百;小船千条,来往如蚁”的壮观景象。
李霁宇中国作协会员、编审。历任云南省作协副主席、昆明作协主席、昆明市文联副主席、《滇池》文学月刊主编、《企业家作家报》主编、云南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等职。在全国及海外家报刊发表文学作品万字,作品收入近百种选刊选本选集合集。个人条目收入近百种辞典。著有长篇小说《壁虎村》、《风逝》、《青瓦——一个家族的密码》及诗集、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集、诗集10余部。作品曾数十次获各类奖。图片、文字版权属原作者!
鸣谢!
文章来源:河口史志非鸟雅书
广告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