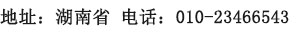文/戴志悦
摄/汤彦俊
几年前的一次门诊中,一对二十多岁的夫妻抱着小孩一进来,对孩子说:“快叫爷爷。”江泽飞一惊,下意识地看一下自己身后是不是还站着谁,助手憋住笑说:“好像是喊您呢。”年轻男子说:“20年前,您给我妈妈看病,那时候我才5岁,今天我带我的孩子来感谢这么多年一直给奶奶治病的医生。”
16岁考入大学穿上军装,不满30岁就开始负责科室工作,年获颁一枚服役35年金质奖章,江泽飞笑着说:“看来,真的老了,都已经是爷爷辈了。”
20年,一名乳腺癌患者看着自己5岁的儿子长大、结婚生子;她的医生江泽飞,从当年青涩的小医生,长成了大医生,不仅站在了中国最高学术讲台上成为中国乳腺癌治疗标准的编写者之一,还走进了St.Gallen国际早期乳腺癌共识专家组,成为国际共识的编写者之一。
近20年,江泽飞与中国乳腺癌学科发展一起快速成长。他说:“一路走来,的确能够体会到,科学发展带动学科进步,学科进步带动个人成长,个人成长反过来又推动学科发展,让更多的病人可以受益。”
赛家有约
用声音讲述生命的守护
本期朗读者:“金话筒”陆澄
肿瘤科绝不是病人通向天堂的候车室
江泽飞实习时是勤快的小江大夫,半夜常会去病房转一圈。有一天晚上,一名晚期癌症患者突然叫住他:“小江大夫,我瞳孔放大了吗?”小江大夫吓了一大跳,“死亡”就这样第一次冷不丁钻进了他的耳朵里,从此与他未来的职业如影随形。
后来他成为了一名住院医师,一个患者半夜去世,同室的病友们都不愿意回病房。江泽飞协助值班护士把去世的患者推进太平间,让护士把那张病床重新铺好,然后他换了身白大褂坐在这张床上,陪一屋子的老太太病患聊天。聊了半天,病友们从负面情绪里渐渐走了出来,说:“小江大夫,你也辛苦了,快回去休息吧。”江泽飞在确认大家都没问题后才离开病房。
“其实,我真的不是很愿意当医生,但我自信我可以当个好医生。”回首30年的从医生涯,江泽飞如是说。
年,他从第一军医大学毕业,分配到军医院(医院)肿瘤科。年,他还是住院总医师时开始带组,科里住进来一位五十多岁的乳腺癌晚期患者。江泽飞和她同住在一个部队家属院子,关系很好。
虽然手里并没有太多的“弹药”,但初生牛犊不怕虎,他不相信“晚期病人不可治愈”。当知道有一种新化疗药在美国上市后,江泽飞仔细研究了文献,建议她可以试试。患者亲人从美国买药带回来,却因化疗药上标注着“毒”而被海关禁止入境,药被退了回去。
“她到最后也没用上这个药,握着她的手眼睁睁看着她走掉,我才明白,我真的不可能治好所有的病人。”江泽飞回忆说。
从此,江泽飞也走上了抗肿瘤新药在中国临床研究和应用的道路。年医院成立了乳腺肿瘤科,他担任科室常务副主任,和时任副院长的宋三泰教授一起,专注于乳腺癌诊疗,这个科室成为国内最早走上乳腺癌专科化的科室之一。
在上世纪80年代之后,乳腺癌治疗从“切得越多越根治”的错误认知中逐渐走出来,内科治疗迎来大发展,尤其二代紫杉类化疗药物的出现,使得化疗效果大大提升。年,二代化疗药物泰索帝进入中国。
中国肿瘤诊疗长期欠下的债,不仅在新药上,也在年轻医生的临床思维上。九十年代后,孙燕院士、储大同教授等人,带领刚刚成立的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的中青年医生们开始参与各种国际临床研究,不仅接轨新药,也接轨临床思维,刚满30岁的江泽飞也是其中一员。
江泽飞:
那个时候,很多人并不愿意搞肿瘤专业,因为医生没有太多的办法,肿瘤科就像无奈地看着病人通向天堂的候车室,更多是临终关怀。但另一方面,新兴学科相对于其他成熟领域,对年轻人来讲又有更多的机会去接触新东西。
孙燕院士等老一辈肿瘤专家,带领我们参与国际研究,训练了一大批中国医生与国际接轨,不仅了解了标准方案,还学会了一个新概念,即合理管理,选择正确的患者。
我们这批年轻人成为最早使用新药的医生,只要你善于用新药,敢于用新药,你的水平会迅速接轨,否则你会走向保守,你可能永远赶不上新的东西。
抗癌治疗需要邦德+邦女郎
年,江泽飞前往美国CITYOFHOPE国家医学中心从事客座研究,两年后回国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受邀在年9月的CSCO年会上做报告,题目是“乳腺癌靶向治疗的未来”。
随后,国际上乳腺癌治疗围绕着化疗、内分泌治疗、靶向治疗的临床研究越来越多,其中有一个著名的代号的大型临床研究,便是化疗药泰索帝与靶向药联合治疗。一直对国际前沿研究保持着同步的江泽飞,在年的一次全国学术会议上,做了“乳腺癌化疗的新策略”的报告,介绍了研究,但同行当时的评价是:“太贵了,中国患者根本用不起。”
年左右,他遇到一名Her2阳性乳腺癌肝转移、骨转移患者,当时医生判断生存期不到一年。这样的患者,传统的方案的确无法让她长期存活,江泽飞与患者和家属商量后,采用了那个代号的联合方案,然后对肝转移和骨转移分别做了针对性的局部治疗。
曾经“想到却做不到”,只能拉着患者的手眼睁睁看着她离去的遗憾,在这例患者身上发生了扭转,“想到并且能做到”,十几年过去了,患者至今依然健在。
江泽飞:
这种患者的疗效可以给医生强大的信心,促使我们不断努力去寻找新的办法,然后反过来又能帮助越来越多有需要的患者。困难会有,但是办法总比困难多,慢慢地,我们不仅可以做到早期病人争取去治愈,晚期病人也可以延年益寿。
靶向治疗进入临床,的确影响思维,改变行为,但在乳腺癌领域很少单用靶向治疗,都需要有很强的结合。就像的电影,再厉害的詹姆斯·邦德,也需要一个邦女郎来配合他,才能战斗力更强,生活也更美好。医疗也是一样,再好的靶向药也需要一个很强的化疗药去搭配,这样的一个组合使得病人有很长的生存。
20年前基本是以手术、放疗、化疗为主的三大传统,随着乳腺癌进入分类治疗时代以后,内分泌治疗慢慢地取得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但化疗依然是乳腺癌治疗的基石,无论精准医学走到哪天,分类治疗走到哪一步,化疗难说再见,无非是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病人中它所发挥的作用。
中国医生不再只是跟随者,而是真正的参与者
中国医生从参与国际临床研究中学习,在吸收中成长,建立了国际化的临床科研转化思维模式,开始自己设计实施临床研究,并开始在国际上发表研究结果,中青年医生迅速成长起来。
“临床实践要跟着临床研究的结果,而临床研究可以改变临床实践。”江泽飞说。
年,江泽飞、徐兵河、欧阳涛等8个年轻人共同发起了一个青年沙龙,他们都是从美国、德国、法国、日本留学回来不久。“北方沙龙”不分东南西北、男女老少、古今中外、春夏秋冬,在这个分享的平台上什么都可以谈,可以是学术相关,也可以撇开专业讲国际形势;谁都可以怼,但不许争吵,更不准打架,开会的时候解决不了,就酒桌上解决。这批年轻人如今都已成为乳腺癌领域的中流砥柱,当初建立的学术友谊,也为未来中国乳腺癌各专业委员会成员之间的合作奠定了的基础。
前几年,“北方沙龙”举行的学术活动上,80多岁高龄的孙燕院士亲手做了一套幻灯,他说:“你们现在都很厉害了,也已经是各科室领导,今天我来给你们讲讲我这50年行医中失败的教训。”他整整讲了40多分钟,“这是老人家给我们这些晚辈最珍贵的财富。“江泽飞说。
在孙燕院士的倡导下,年江泽飞执笔和全国乳腺癌专家一道,将美国国立综合癌症网络(NCCN)的《乳腺癌临床实践指南》引入中国,这是在美国医学界被公认的乳腺癌治疗方法。十年后,中国专家正式起草颁布了中国乳腺癌临床实践指南。
年江泽飞收到一个邀请,询问是否愿意作为中国的医生代表来参与国际乳腺癌诊疗共识的讨论。
“当时我有点不敢相信,为什么是我?”江泽飞说。第二年,他作为首位华人进入了St.Gallen国际早期乳腺癌共识专家组成员。随后几年,邵志敏教授、徐兵河教授也先后受邀加入这个专家组。拥有了国际共识出台的投票权,这就意味着,中国的肿瘤医生不再只是一个跟随者,而是参与者,从跟在别人后面跑到一起跑。
近年来,医疗人工智能方兴未艾,江泽飞已经组织国内多中心乳腺癌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研究,并收获宝贵经验,他说:“从经验的积累走向了循证医学的探索,从精准医学走向智能医疗,正好也是我这20年医疗实践和探索的过程。”
“20年很短,也很长。”江泽飞说。
戴志悦:医生的成长必须经历较长的时间,而你30岁就当科主任,这种快速成长有没有什么遗憾的东西?
江泽飞:有,青春短暂。别人还可以大树底下好乘凉,把所有责任都让上级医生来承担时,我早早就要承担科室的责任了。我的老师宋医院副院长,他说:“你工作上要向我靠拢,生活上可以跟年轻人靠拢。”所以现在我喜欢和年轻人在一起,让自己稍微年轻点,因为我的青春早早就被抹杀了。
宋三泰老师是我人生的第一位贵人,他要求完美得近乎于苛刻,比如夏天值班科室收一箱雪碧都要挨批;收病人往往要我收重病人,老师说了,别人不愿意干的活你要干。这些经历,虽然很艰苦,也很辛苦,但这种历炼对年轻人成长很重要,也很必要。
后来又幸运地遇到孙燕院士、张嘉庆教授、沈镇宙教授等贵人,遇到秦叔逵教授、马军教授等CSCO学会领导。尽管我不是出自孙燕院士门下,但他对我们这些晚辈都像亲学生一样提携栽培,给我们机会,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经验教训教给我们。
戴志悦:很多医生可能不记得治好了多少病人,但会记住让自己遗憾的病人。
江泽飞:当医生就是一种遗憾的艺术。病人少的时候,医生能有时间围着病人转,但现在病人太多的时候,住三五天就出院。病人治疗效果不好的,也不再找你,回来找你的,基本都是治疗效果好的病人,会回来感谢你。一百个病人你治好30个,十年就是个,一天一个人感谢你,就是天天有人感谢你,送锦旗、送鲜花,你就有可能会沉浸陶醉于其中,而迷失自己,更不会去想没有回来找你的那70个人,治疗有没有问题,问题出在哪里?
戴志悦:男医生面对那么多的女患者,工作中会不会尴尬?
江泽飞:这个问题杨澜女士也问过我,说,你们有名的医生都是男的,我们女性看病怎么办?我说,你去餐馆吃饭,你会在意给你做菜的厨师是男的女的、胖瘦高矮吗?其实,男医生在乳腺科,反而可能有一定的性别优势。在某些时候男医生在这个学科里,可能会让患者更有亲切和信任感。
戴志悦:查体的时候呢?
江泽飞:西方国家医生要给患者查体时,会问一句:“我能不能给您查体?”我刚从美国回来时,也这么问来诊的老太太,结果病人说:“你真逗,我来就是要找你检查的,你还那么客气。”所以这是一种职业习惯,也是一种文化观念的问题。
我觉得专业的触诊,尤其面对晚期病人的时候,医生的肢体触碰,比如握握她的手、拍拍肩膀对她们很重要。我查房时,有些病人说肩背疼得厉害,我说那我给你捏捏好了。然后就真的帮她捏,捏完后问她感觉怎样,她说很好,我说下周查房我再给你捏,其实她的生命也可能等不到下周了。
戴志悦:你很“宠”你的患者。
江泽飞:这30来年,我看了不下10万个病人,也就旁观见证了这么多的女性的人生。她们的婚姻、家庭会遇到各种问题,有的人一诊断出来就离婚的,也有至死不渝的,甚至还有治了十年,病人走了才发现身边一直照顾她的那个是已经离婚多年的前夫,他说:“听说她得病那天开始,就觉得要照顾到底。”
有一位老太太,治疗好几年了已经快到人生终点了,最后的两周基本上没用药物治疗。老伴儿陪着她,天天看他们年轻时候的照片,感觉很幸福的样子,她在等着女儿从新西兰回来。医护人员和患者平安夜联欢,我和她手拉手合唱了一曲《明天会更好》,之后不到一周她就离开人世了。还有些病人在电视上看奥运会,我们开玩笑说:等着在北京的现场看奥运吧。其实,她真熬不到那一天,但我们要给她希望,哪怕是假的。
谁都希望长命百岁,但谁也不可能如此。医生治疗晚期病人这种不可治愈的病人时,能帮她完成阶段性目标,给她一段精彩人生,尽可能帮助她们人生无憾就可以了。
戴志悦:患乳腺癌不仅仅是在对死亡的恐惧,还有失去乳房的痛苦。
江泽飞:失去乳房对女性是生理和心理上的双重打击,所以我回国第一次演讲就说,人人都有保乳的权利,切除需要理由,保乳无需理由。
当时有同行说,我们讲半天保乳,病人不愿意保乳怎么办?我说,保乳是不需要理由的,就像我说你腿上长个包,你就把腿锯了吗?房子一个柱子坏了,你就要把房子拆了?所以只要你有保的念头,你才有机会保下来。
还有人还说,东方女性乳房小,切了无所谓。我说,小才更珍贵。
曾经在一个学术会议上,讨论是否切卵巢的问题。一个年轻的女医生说,应该切,卵巢留着也没用。我当场就说:“这句话从你一个年轻女医生嘴里说出来,我觉得挺遗憾的,作为年轻女性,你更应该了解失去乳房和卵巢对女性的痛苦。”
所以,应该真正从尊重生命的角度去尊重患者的感受,尤其女性的乳房、卵巢,这是她的第二性征,千万不要认为有它没它无所谓。
戴志悦:医学人文最重要的就是唤起医生的同理心,因为当医生久了以后,很难站在病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江泽飞:毕淑敏写的《拯救乳房》,把众多乳腺癌患者的悲惨故事写在一本书里,一下子看完,很多病人和家属都受不了。所以,这本书是病人可以慢慢看,家属可以看,但乳腺专科的医生和护士一定要好好看,看完以后你会知道乳腺癌病人有多么不容易。
但站在医生的角度,我也不希望医生视病人为亲人,否则你会很痛苦,设想如果一晚上送走三个病人,想同时送走三个亲人,你还能擦干眼泪微笑面对下一个病人吗?
戴志悦:总体来说,乳腺癌还是比较好治的吧?
江泽飞:是的。沈琳教授以前说过,当年她还在跟着金老师一起工作时,治胃癌治得不来劲时就收两个乳腺癌来提提士气,因为胃癌患者治半年可能就走了,而乳腺癌至少能治三五年。
其实对我们乳腺专科医生来说,最大的挑战,我们有能治上十年二十年的病人,也有治了半年就走了的病人。亲身治疗过一位年轻的女军官,从诊断到离开,也就一年的时间。我们用尽了一切可能的手段,还是只能无奈目送她离去,那时候我对自己说:别老在讲台上说我们能让癌症治成慢性病,其实我们能做到的远远不够。
治了那么多患者,一到过节肯定会收到感谢短信、电话之类的,千万不要以为都是你治好的,其实可能人家的命本来就挺好的,谁治都能这么好,只是因为你名气大人家找你看而已。你可能也是运气好,看到更多好治的病人,碰到更多愿意配合治疗的病人,遇到能承担得起治疗费用的病人,仅此而已。
其实肿瘤治疗,有命和运的关系,有的人命好运也好,有人命不好但是运好,还有人是命和运都不好。命是天定,而遇到的医生水平、科学发展到哪个阶段、有没有强大的支持等,就是运了。
医生当得越久越会觉得你能解决的问题是有限的,千万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
戴志悦:所以好医生是越当越谦卑。以前有一位80多岁的医生,他在自己的一本专著的前言中写道:当医生这么久才发现自己能解决的问题越来越少。
江泽飞:我觉得是应该的,这是一种对生命的敬畏,发现自己能解决的问题越来越少,但你能帮助的人肯定是越来越多。随着你经验的积累,患者第一时间能找到你的话,你就能给他指一条很好的路。
虽然,生命的长短老天已经定了,但你可以帮助她过得长一点,过得好一点。我经常会跟病人说,你活多久或许是老天定的,你能不能活得好咱们可以争取。
影视剧里总看到医生说“你还能活多久”,其实医生往往看病不算命,我们不可能准确计算出生命长度,因为我们拿到的数据大多是中位值或平均值,而每一个病人都有可能争取活得更长。
十多年前我去外地开会,讨论一位患乳腺癌的71岁老太太病例。有一位医生说:“已经71岁了,治不治也就这样了,中国的人均寿命就71岁。”会后吃饭时,我特意找到他说:“哥们儿,咱们人均收入就5万块钱,你有5万块就不挣钱了?”他说:“那不行。”我说:“那你凭什么说老太太活到人均寿命就可以不治了?”几年后我和这位同行再遇到,他说:“你的话对我影响太大了。”
医生所谓的喜悦和成就感,就是来自于你能帮别人解决一些问题,比如帮她们放下心里的负担,纠正一些不必要的治疗,提供一个正确的医疗方向,或者让她们存活的时间尽可能长一些。
我常说:我不一定治得好,但我一定好好治。
感谢志愿者黄锦花对文章进行校对
第1期:孙燕:对于肿瘤治疗未来,我是乐观主义者
第2期:廖美琳:肿瘤治疗没有百分百,都是一步一步爬着过来
第3期:沈镇宙:医生“站在床边”,病人“躺在床上”
第4期:张嘉庆:乳腺癌是肿瘤治疗“百科全书”
医生医事原创文章,转载请联系授权
戴戴(戴志悦)
独立医学人文记者
《遇见肿瘤名医》作者
曾任人民日报《健康时报》编辑部副主任
曾任腾讯健康频道副主编
新书购买
全国各大新华书店、医药科技书店
淘宝、当当网、亚马逊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