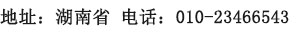来源网易号‘徐佶周’
采写:刘功虎
受访:方方
方方获第十届华语传媒“年度杰出作家”大奖,是因为小说《武昌城》的杰出文学成就。
授奖辞称,方方的小说“以柴米油盐的庸常,暗喻激情过后的空洞,以生命的弱,见证人的复杂、悲壮、不可摧毁……以慈悲与宽恕之情,回望革命的成败,攻与守,大与小,高贵与卑贱,理性与冒失,皆有平等的地位……去理解人而不是去判断历史,去发现个体的价值而不是去给群像命名,方方庄严地完成了对一座无城之城的精神确认”。
方方生于南京,但是她的全部记忆与武汉紧密相关。她高中毕业后曾在武汉运输公司当过装卸工,熟知底层生活。她具有武汉女性特有的泼辣、乐观、快人快语的风格。
也许是因为在底层“打拼过”,也许是因为在电视台工作过,她对待媒体一直持有开放的心态,几乎总是有求必应。不少记者胡乱篡改过她的言语,甚至张冠李戴,以莫须有的理由诋毁她,造成很多生活上的苦恼,她还是坚持“不设防”。
这种品质似乎均超越了一般武汉人的地方性人格,融入到了世界潮流。
刘功虎: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与鲁奖、茅奖有什么不同?在你心里分量如何?
方方:鲁奖、茅奖应该算是官方奖,各地政府器重,给作家个人带来的利益太多,这样就难免会有很多因素干扰。比如某种题材必须要有,以及与中国作协的关系等等,还有评委也比较杂,有的人不一定是正经专业人员,不少人对文学半通不通,长期做行政管理工作,也充当专业人员参与评奖,这就造成判断不准的结果。
而华语文学传媒奖带有民间奖的性质,其理念比较纯粹,是一些真正做文学的人在评,它在作家心里的位置应该更重要点。奖金不算高,但是,钱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你的作品得到了什么人的认可。
刘功虎:《武昌城》写的是年左右北伐战争的故事,书中写了战争带给双方的痛苦和撕裂,你怎么看待历史上形形色色的战争与革命?
方方:这本书写的北伐战争中的武昌战役,北伐军攻城,北洋军守城。这是一场相当惨烈的战事。它死的不仅是数不清的军人,同时搭上了无数无辜的老百姓。战争让所有人受了重创,无论军民,无论身心,其伤害程度,都无以言说。当年的战场,现在几乎是武昌的中心。那些地名但凡武汉人都耳熟能详,只是我们都不知道这里曾经是鲜血淋漓的战场。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武汉人都不知道历史上有这样一个围城事件。对我来说,我的敌人是战争本身。我是站在人的立场,即我既站在攻城一方,也站在守城一方。而战争双方,彼此各有心态,各有理念,各有曲折,各有命运。对与错的评判不必由我说,这是历史学家的事。我所 刘功虎:有观点认为,我们的民族比较缺乏妥协和反思,因此你死我活、成王败寇的悲剧频频上演。《武昌城》里那些矛盾冲突的人物要是放在欧美语境下可能很好理解,但是放在中国未免总让人有些疑惑:我们的历史上有过这种人吗?防失联看更多请加 方方:有疑惑吗?你可能低估了读者。在历史上,这样的人物多得是。在任何历史阶段,任何人群中,都会有一些正人君子。他们有着美好的个人品质。比方北洋军官马维甫,他本是一个人本主义者,也满怀理想。在他看到武昌百姓陷于痛苦之中时,他想营救他们,而他所受的教育又使他不能随意叛变。他必须忠诚,必须恪守职责。所以他的内心一直在挣扎。良心和人格在冲突,在打架。这两样都是他想要的,但他要一样就得放弃另一样,他不知如何选择。他想救百姓,但又不想毁掉人格,他想保全人格,却又不忍让百姓受如此之苦。最后他选择了良心,但是他自己却遭受灭顶之灾。
我在后记中曾经写道:“守城和攻城,各有自己的角度,各有自己对事情的看法,也各有自己的痛苦和悲伤。战争将人性中的大善大恶都张扬了出来。我相信,无论革命军还是北洋军,当兵从武,有人是为了解决饥饿,有人是为了反抗压迫,有人是因为天性尚武,也有人就是无可奈何。但亦有一些人,为的就是理想。这理想便是希望中国有个美好的未来,希望能参与自己的一己之力让自己的国家和平安宁。他们的理想是相同的,只是选择不同结果也全然不同罢了。”
我很清楚,但凡战事,都有它对立的一方。而身处于任何一方的人,都有他自己的理由。就是我们通常所认为的敌人,他作战的理由也未见得就是从恶出发。敌人和坏人是两个概念,而自己人和好人也是两个概念。所以,正义和非正义以及好人和坏人,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层面。人的思想和性格是很复杂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是很复杂的。作为写作者,我应站在他们各自的角度、按照他们的思想逻辑设身处地写出各自内心深处的感受。
刘功虎:在历史的本真和个人的希求祈愿之间,你怎样权衡取舍?
方方:这样的创作,的确很考验自己的控制能力,同时也考验自己对历史的判断和把握。但我只需真实地表达就可以了。我在开始写作之前,因阅读了许多回忆录,所了解的细节也算比较多,所以在动笔后,我力求将这些细节复原在小说中。大的史实(包括时间、地点、方式等)和生活细节(包括食物、生活场景以及物价等)尽量让它真实。虚构的只是活动在上面的人物。历史场景,在我脑海里就是一张巨大的画面,所有的事件人物,都会清晰地呈现在上面,每一个细节都真实。而画面总是有空隙的,我只需要将我们的人物放在这幅历史画卷的空隙中,让他们在其中参与,并且出现在每一个节点,让他们成为其中一员。这就可以了。
刘功虎:你参与成立华科大当代写作研究中心,邀请名家与学生面对面交流,这会不会挤占你的创作时间?
方方:一年中无非花一个月的时间来做这样的事。我觉得这也是应该做的事。作为一个文化人,或是作为一个作家以及一个作协主席,是很喜欢自己生活的城市有着浓郁的文化氛围的。而文化氛围其实就是一个一个的文化活动所形成的。我们的活动,主要在大学内。我希望通过这样高水准的文学活动,引导大学生认识什么才是真正的文学以及什么人是真正优秀的作家,同时也是让这些优秀作家的文学理念能够传达到更多的年轻人那里去。
刘功虎:你在大学教授和作家两个身份之间是怎样取舍平衡的?
方方:不需要做什么平衡,因为也花不了多少时间。按时间顺序,认真做就是了。
刘功虎:在我的印象中,很多作家都是“孤独的动物”,很个人主义。但是在你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种乐观的、合群的积极心态,这是个性使然?
方方:那是你的印象有误区。小说写得不好的人,才会把自己装得与众不同,仿佛向人宣告,只有我这样,才是作家。你可千万别信。我见到的大多作家都跟大家一样,是很正常的一个人。乐观合群者多得是。尤其优秀作家,真没几个装模作样的。我只不过是其中一员而已。
刘功虎:你在接受凤凰卫视专访的时候提到,在中国历史上,作家从不像现在这么不招人待见。
方方:我可能是说,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喜欢骂作家。其实这是个事实。以前没有网络,大家没有说话机会,现在有了网络,人人可以发言。骂别人不方便,你能骂你的领导吗?能骂公安、司法吗?尤其点着名骂?只有骂作家最省心省事。作家有名,同时作家又不还嘴。大家骂起来很开心,当然都喜欢骂了。其实作家也无所谓,生活这么辛苦,这么多人想要发泄,由着大家骂骂也无所谓。再说了,作家中至少一半人也实在应该骂。防失联看更多请加 刘功虎:你觉得武汉人像美国人,为什么这么说?
方方:说武汉人像美国人,这完全是说笑。只是某一方面有点像而已。就是武汉人说话不拐弯抹角。武汉人说话直率,不屑让人听话外之音,喜欢把话说在明处,这是我最喜欢武汉人的地方。但要拿武汉人跟美国人相比,实在也不好比,因为彼此生活的社会环境完全不同,不具备那样具体的可比性。
刘功虎:前段时间你“一不小心”还曾被卷入韩寒事件当中。此次韩寒小说《,我想和这个世界谈一谈》似乎并没有得奖,你觉得与他被质疑代笔的风波有关系没?
方方:我被拖到韩方之争时,根本都没弄清楚怎么回事,只是在搭人话时,被揪了出来。韩寒的小说有没有得奖,或是能不能得奖,这是评委的事,跟我毫无关系,我也没有读过他的这部小说。
我支持韩寒,首先是我认为新概念没有一点造假,我是当事人,我很清楚。其次是,我认为韩寒的作品是他自己写的。这是个简单道理,他父亲写不出这样叛逆的文字,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任何人站出来说韩寒的作品是他代写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理由认为没有代笔。
在现今这样的社会,年轻人应该大胆发出自己的声音,应该有自己的生活理念。这点韩寒做得不错。而我看到更多的年轻人满嘴假话,媚上欺下,一心只想往上爬,这样的人太多了。跟他们比较起来,韩寒就显得十分可贵。年轻人要大胆发声,大胆亮出自己的人生态度。
刘功虎:你曾认为80后作家普遍偏于幼稚,“10个人放一起起码有8个人是差不多的”。现在,你的看法是否有所改变?
方方:这是好多年前说的话,那时的80后不过二十岁出头。因为没有阅历,作品比较雷同,他们的童年期比较漫长。但现在,他们中很多人大学毕业了,参加了工作,有了不同的阅历,他们开始长大,成熟。80后作家也有了越来越多的好作品,相信很快我们就能读到他们更厉害的作品。
本文选自《有些问题我想清楚了》,长江日报传播研究院编,武汉出版社,年4月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