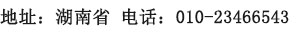交口村往事
冯建平
交口村位于离石城西南5公里处,自战国赵置离石邑以来,经秦汉历隋唐至宋元明清,皆属离石(石州、永宁)境。交口,顾名思义交会之口,大抵有川交汇者名之、有路交汇者名之、有水交汇者名之,而离石交口独为川、水、路皆交。但是何人所名?名于何时?今人已无从知晓。所幸离石区红眼川乡西山里村有元至正六年(年)《重修虸螯庙记》各村施钱名录碑刻一座,其碑阴就刻有“交口村张仲才”,这是迄今发现关于交口村名最早的文字记载。
交口村南有河,名南川河,据洪武《太原志》载,南川河其源为车辙泉水,在宁乡县南四十里,流至县北入石州界。又《清统一志》载,汾州府安乡水在宁乡县北又名清水河,北流入永宁州名南川河,合离石水,因河出宁乡县故称之为县河。交口村北还有一条河名叫文河,乃北川与东川两水合流而成,因离石旧为州治故又得名州河。这州河之水,河道宽敞,水面平缓,鸣禽水鸟,翱翔水面,鱼蛙浮生,上下浮沉,山光水色蔚为大观。而县河之水,涓涓潺潺,清澈见底,岸柳摇曳,啾鸣相应,妇女浣衣,儿童戏水,耕牛牧笛,不绝于耳,仿佛一幅山水园林之画。两河之水在交口村汇流后,名曰三川河,曲折向西流入黄河。两河所过之处,河道数易,沙土淤积,经年累月,杂草纵横,狐兔巢穴。幸有先人披荆斩棘,栉风沐雨,拓家园于荒野,立交口村万世根基于斯地。
一
交口村位于三川河河谷,依山傍水,大得两河之水恩泽。村中人畜饮水皆以凿井为主。二三十年代,全村共有桔槔井2口,辘轳井1口。桔槔井一口位于当街(已毁);一口位于背湾,是离石现存唯一的桔槔井。辘轳井则位于旧戏台以南至今仍在使用。此外,交口村疏渠筑堤、引水滋田更为悠久。据民国七年十二月,离石县渠道调查情况显示:当时交口村与段家坪、高家沟三村合资自城西莲花池下引水开渠十数里,渠深三尺,宽五尺,经段家坪、高家沟到交口。按地亩交口村分摊了全渠年三百一十五千文的维护费。为扩大水浇地面积,二三十年代交口村又与邻村合作开渠两条:一条自马茂庄经高家沟、石盘、枣架到交口,另一条自西合村经韩家坡、圪垛到交口。旧时,骑河筑堰,跨界开渠,村与村争,稍有不均,便会引得千百之众群起而攻,或执械相搏,或叫嚣于公堂,而交口村人总能以公允之道,取信于邻村,鲜有水案纠纷发生。当然,大旱之年,村中亦会选拔精悍之人,昼夜巡渠,遇有蛮横之徒,越河越界,肆意强开,则以实力相应对,使其知难而退。交口人保住了水资源的支配权,祖祖辈辈也就解决了自身的温饱问题。当然,捞河柴、捡地皮菜、挖沙、捡石头发点“靠水吃水”的小财,就更不在话下了。然而更多的时候,交口人面对的却是洪水来、灾情到。据离石县志载,民国三十一年,县域连降大雨,南川河暴涨,房窑倒塌,良田被毁,水患之大,闻所未闻。面对肆虐的洪水,无奈的交口先人除了跪在龙王庙里祈求神灵保佑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洪水将家园冲毁。
(桔槔井)
龙王庙位于交口村庙坪上(今交口村扶贫焦化厂一带),始建于何时,已无法考证。据村里八十多岁的刘根年老人讲,交口村历史上古木参天、水草丰茂,相传盖龙王庙时用的椽梁都是就地采用。庙前有两棵松树,有成人三四围之粗,村人称大王、二王。神庙坐北向南,东西各有三间石窑洞。每年七月七庙会,唱戏三日,费用由圪垛、交口两村分摊,其中交口摊2份,圪垛摊1份。当年龙王庙附近还有五道庙、山神庙、河神庙,后来除山神庙的神像在解放后,因水患被村人付候六转移到山上外,其他庙宇都被洪水冲毁。
关于山神庙的迁址,村人至今相传当年付候六背负山神像,行至今山神庙址一带,忽感神像重若泰山实在无法前行半步,遂就地于崖上安置佛像,供村人祭祀。这个美丽的传说多少年来已在交口人的心头生根发芽,以至于每年农历的二月二山神寿诞日,村人都要举行盛大的娱乐活动,祈祷山神监管山中猛兽,保护全村人畜平安,风调雨顺。
与山神庙香火兴旺形成巨大反差的是,年,洪水把位于庙坪上的石拱桥、付家西院里以及龙王庙一并冲毁后,龙王爷的灵验程度遭到了年轻人的质疑。对于年轻人的质疑,老辈人是有不同的看法,六十年代保牛、二牛两兄弟被困洪水中,虽说是村中健儿渡水救回,但老人们说,没有保牛奶奶跪求龙王爷保佑,就是去上几十个人也救不回来。姑且不说龙王爷的灵验程度,大旱之年,两河干枯,村人求雨,三牲齐备,虔诚之至,天地可鉴,然天雨不至,十年九旱,即使主管风调雨顺的龙王爷也无可奈何。村人无奈只能团结起来,打井灌溉,抗旱保命。据离石县志载,打井灌溉是从清光绪四年连续大旱后才被重视,但为数极少,仅为少数富人所有。民国三十年《离石县政年刊》也载,本县春夏,天火不雨,旱象将战,省署拔国币元,助民凿大井5眼,小井15眼,村民自行筑成30余眼。而当时交口村庙坪、中滩、上河滩、阳湾、圪针湾就有井6口,现今交口村文史馆就保留有民国十二年,村民刘世广、冯满俭、付尚发、付玉保在中滩上合资打井契约1份,契约内容为:“立约人:刘世广、冯满俭、付尚发、付玉保,情因义气相投,同议凿井1孔,于州河中滩上冯满俭地内,俩出情愿,日后井儿不废,不准出买归属他人之流通,冯满俭地亩10亩,刘世广地亩3亩,付尚发地亩5亩3分,付玉保地亩6亩半。以上共地亩24亩8分整,按以亩数公摊每亩摊钱陆千文,共摊钱一百四十八千八百文整。此系两厢情愿并无异说,恐后无凭,立约为证。”此井一直沿用至交口商业街建成,方归户主所有。
正是依靠打井灌溉,交口人在大旱之年仍然顽强地生存下来,然而面对山上枯萎的禾苗,村人只能听天由命、束手无策。祖祖辈辈引水上山的愿望,是在年交口村圪针湾电灌站建成后才得以实现,电灌站一级扬水,总扬程米,装机1台,16.17千瓦。村人则投资在山上建成了m3蓄水池(又名胜利池)1座,此项水利工程,设计灌溉面积亩,可灌溉面积亩,只因灌溉成本过高,很少运行,改为养鱼池,由村人冯润山看管。改革开放后,土地使用权归个人所有,水管等设备遭到破坏,胜利池于是也就荒废了。
二
交口村地处水陆交汇之地,自西可去柳林、陕北,向南可达中阳、晋中,往北直抵方山塞外,然而州河与县河交汇造成的交通不便,一直使交口村的位置优势无法得以发挥。直到年,太军公路开工,一座五孔石拱桥在交口村建成后,一个辐射周边的商品集散地才慢慢形成。对于那座影响交口村近百年经济走向的石拱桥,今人只能从流传于离石的民间快板书“民国十年修路工”中领略到大桥的风采,快板书是这样说的:“交口人着了急,毁了好地舍不得;交口河口盖大桥,工人齐往桥上跑;盖大桥的广东人,携的石头平又平,逼水珠,是宝贝,龙头虎眼是一对”。在权衡了“好地和大桥”谁更能改变交口人的命运后,着急的交口人选择了后者,从此位于交口村的官道上驴、骡、骆驼昼夜川流不息,交口村成了全县驼运路上延续时间最长、驼运量最大的一个的商业枢纽。依托这条商道,交口村商业开始兴盛起来。据离石县志载,民国二十五年,全县有粮食加工业15家,交口有一家即兴盛魁商号。兴盛魁商号创办于民国二十年,由村人冯满俭的四个儿子集股兴办,四子冯堂兴与女婿高能富负责运营,主要经营磨坊、染坊、货业坊,俗称三杂坊,后兼营典当业务。现交口村文史馆就保留有民国政府山西省财政厅印制的兴盛魁税银收据1份和晋绥财政整理处颁发的营业牌照2份,以及胡邦有、张林成、付治有典当契约3份。另一家被载入县志的是民国二十一年由村民刘世广独资创办的粉坊1座。粉坊资本30元,工人4人,年加工绿豆石、薯类斤,产值元。除兴盛魁商号和刘世广粉坊外,县志还提到,交口村康老大和付赶年(三和店)的车马旅店以及付玉芳饭店。当然没有载入县志的商户也不在少数。据村里多位老人回忆,清末民国时期交口村还有:任培厚的大德茂(烟坊)、姜世昌的太和兴(药店)、付安邦的义盛泉(货业)、李正营的源盛昌(饭店)、付长喜的三义久(饭店)、付玉荣的三义香(饭店)、付玉山的源成茂(染坊)、刘汝荣的德盛堂(染坊)、张光牛和张光朝的染坊、尤克仁和尤克宽的铁匠铺、黄秋顺的理发铺、张安泰的磨坊等二十余家商号。
交口村成了方圆百里的商业中心,只可惜这样的繁荣未能持续多久就被日军侵华战争所打断。据老八路冯氏后人冯成生回忆:年农历正月二十五日晚,日军占领交口后,将各商号洗劫一空并纵火焚烧,兴盛魁磨坊磨面用的磨盘都被烧成了几块,众多商户被迫关门歇业。在缺衣少食的困境中,村民们无钱,也无处可买生活用品,而日伪政府却在交口成立了“离石县第一区天口村税务征收分局”,并强迫村民筹集资本设立合作社,实行商品配售,贩买民众日用品,对广大村民极尽盘剥之能。现交口村文史馆就保留有民国三十年,冯堂兴股本证和村民杜德昌、冯堂昌等贩卖牲畜的纳税收据各1份。在日占领期间,为支援阳山武工队打击日寇,以付玉宁、付安邦为首的交口村商户,对敌人强行摊派的粮款软拖硬磨,少交或不交,而对党组织分配下的布匹、粮食都如数送到芦则峁村,交给一区工作人员李丕贵,从不拖延,总能按时完成任务。
交口村的七月龙王庙会始于何时已无法考证,但龙王庙前“大王、二王”那两棵老松树的传说,足以说明庙会的悠久。交口村集市庙会的兴衰可以说是村经济发展的缩影。解放后,交口人民挣脱了几千年的封建枷锁,在党的领导下,政通人和、百废待兴,原本萧条的集市又日渐繁荣起来。那时候一到赶集的日子,各种山货、粮食、农具堆得满街都是,方圆几十里来的群众把街道挤的满满的。据村中老人杜如玘回忆,离石解放后,贺龙同志好几次坐着敞篷吉普车下柳林,只要遇上交口村庙会,都要停下来,让几个馋嘴的小警卫员去尝一尝王生成的饼子和胡大妈的绿豆旋粉,还让小孩子们带着警卫员去水久滩打过野鸭子。他自己则坐魁星楼前二小(高家沟村人)的饼子铺前,嘴里叼个大烟斗,和乡亲们拉闲话。后来国家实行了计划经济的政策,集市贸易一度萎缩。改革开放后,集市庙会重新繁荣了起来。特别是庙会已经转型为一年一度的农村物资交流大会。会期也由三天变为十天或超过十天。每逢集会,商贾云集,万头攒动。有卖锅碗瓢盆日用品的,有卖红枣核桃小杂粮的,有相亲催账走亲戚访朋友的,有看手相算命捏玛子卖牲灵的,有搞展览放录像耍魔术的,还有唱晋剧演电影弹三弦助兴的,真是应有尽有、无所不有。市场的繁荣使原本宽敞的旧街显得十分拥挤,于是集市便转移到新落成的商业大街。交口村商业大街,始建于年,年商业街与横跨洲河的人民桥一同竣工。商业街建筑面积7.12万平方米,拥有个门店。商业大街建设期间,山西省省委书记王茂林、省长王森浩,以及梁国英、王文学等省领导多次来交口村视察工作。年7月5日,时任中央委员的温家宝也来到了交口村,热情地称商业街为“北方农民城”。
(温家宝在交口)
交口村商业经营一直都是小而全,形不成规模。改革开放后烟草与面粉的经营一度影响周边数县,辐射陕北吴堡,但随着国家烟草专卖制度的完善,以及物流与信息业的发展,面粉与烟草的经营逐步淡出市场。近年来,随着龙凤大街的南移,村商业大街二期工程的完工,以及离石、柳林、中阳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交口村又一次迎来了经济发展的春天。
三
独特的地理条件造就了交口村在军事上的重要位置。五六十年代,交口村发现了一条古战道,战道自背湾沿山脊直达阳湾山上,村民冯水才、李保牛以及刘根年、付天有家的旧址都有入口。战道始建于何时,因何而建,何人所建?没有人知道,也无史料可查。据村中老人刘根年回忆:解放后,自己和村民李奴生、付侯七曾点火把,持七九步枪从李大保家后沟(胶泥沟)钻入洞中,洞高不足一米,人仅能猫腰通行。三人行约半个多时辰,有三个岔洞出现,怕迷路遂返回。
(交口村古战道)
此外在交口村崔候锁住宅处出土的东汉河东掾丞西河平定长乐里吴执仲墓与中阳县道棠村和平元年故中郎将安集掾平定沐叔孙墓相距不足千米之遥,近年来又在书房洼发现明代“楚庄王赠只将军”的冥柱,这些中央和地方军队要员墓以及古战道在交口村一带的发现,充分说明了交口村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这或许就是交口人民从来就不缺乏斗争精神的原因吧。据《离石文史资料》载,民国二十三年春,交口村部分村民(十虎兄弟)在离石名人任培厚及其子任绪,其弟培元、培辰的带领下为反对盐店的剥削,同周边数村百姓打了离石官盐局,这是交口村民有文字记载的第一次反抗政府的行动,在离石的史册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年4月11日,东征红军第二十八军在军长刘志丹、政委宋任穷的带领下进驻交口,军部设在付家大院。付家有田地近千亩,佃农遍及邻村,以付飞威、付飞雄、付秉益、付能显、付尚发等最为著名,为清末民国时期交口村首富之家。特别是付能显的女儿付玉珍,是中共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贺昌同志的继母,付玉珍曾就生活问题上书毛泽东主席。后中央内务部协同山西省民政厅来离石调查了此事,并责成当地政府妥善安排了付的生活。最值得一提的是,现中央档案馆仍保留有红十五军团攻占金罗朱家店后,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电告红军总司令彭德怀、政治委员毛泽东“攻击朱家店、金罗镇情况”的电文。电文中就有红二十八军在交口宿营的内容。在交口村东征红军打土豪、分田地,宣传党的政策,村民付春海积极为红军带路,抗日的火种从此播撒在交口村的土地上。
年秋天,战总会武新宇组织的工作组和牺盟会的同志经常在交口村宣传抗日救亡工作,侯玉章、付明华、尤克宽、杜锡禄等青年积极响应,成为光荣的牺盟会会员。杜锡禄等还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年2月,中共离石县委在交口村神楼前,召开了离石县农民抗日救国联合成立大会,会上交口群众情绪高昂,决心为保卫家乡与日寇作坚决的斗争。神楼位于交口村当街,始建于何时已无法考证,幸有清乾隆丁亥(年)碑刻可知神楼历史之悠久。神楼下有门洞供行人车马通行,此门洞后因四围地形抬高,遂掩埋于地下。清末民初,有佛家弟子张根清在此守楼,晨钟暮鼓,是村人心中的“圣地”。不过无论交口人多么虔诚地祈求和平,无论神楼里高高在上的关老爷多么神勇,都未能阻挡住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同年2月,侵华日军谷口茂联队进驻离石,为牢牢控制离石至军渡这条战略交通线,鬼子在交口村崖上(地名)成立了专门对付八路军的防共青年团(即红部);在村东南堡梁(山顶呈馒头状,东高西低是村制高点)筑起了坚固的碉堡。然而,鬼子的高压政策并未吓倒抗日的军民。年12月31日,晋军第19军71师夜袭盘踞交口、李家湾、金罗、一带日军,日军伤亡90余人;年农历七月,离石大汉奸车某被一区游击队杀死在交口桥下;年农历七月十九日,打入敌青年团的交口村地下党员付玉殿(小名付成孩),配合八路军某连在红部设伏打死一名日军,为掩护群众,付玉殿被鬼子抓到城里,并于农历的八月初八在交口当街打谷场将其杀害。在以后的岁月中,交口村儿女前赴后继,在党的领导下,书写了许多可歌可泣的革命故事。在解放离石的战斗中,年仅十七的民兵冯福荣、尤探锁光荣牺牲;张家谟(伪县长)、狄予公(统委会主任)、杨汶(爱乡团团长)等在村西南山上被活捉;在晋中战役中多伤病号来到交口,全村多妇女,捐鸡蛋、香烟,照顾伤病员;在抗美援越的战场上,小学教师白树武走出国门勇敢地打击侵略者;在交口冯英英与二军团四师红军干部王德荣喜结连理。还有许多英雄的故事,我们实在无法一一讲述,不过有一些英雄的名字我们却必须永远铭记。他们不是交口人,却倒在了这片土地上,他们就是年被鬼子在碉堡里杀害的武工队员姜生山和在村中捕杀的战士于殿英以及被阎锡山军队杀害的民兵闫天桂,愿烈士们永垂不朽。
四
清末交口村富家利用冬闲季节,请先生对子弟施教,自办冬学,称为冬书房。民国七年,离石推行《山西省实施义务教育规程》,50户以上村庄必须办学,规定学龄期儿童必须接受国民教育,对无故不入学的儿童家长处以罚款,各村纷纷开办国民小学。据村中老人李成章回忆,二三十年代全村约有90余户人家,左右人口。国民小学设在当街神楼内,学生不足20人,不分年级,课程有国语、算术。教师先后由离石高等学校毕业的村人付玉环、付尔贤以及韩家坡韩守恒(山西农大毕业)、刘家沟村冯金柱(字凌云)担任。
年春,日伪离石县政府强迫交口村开办了“天口村新民小学”。关于日伪政府更名交口村为天口村一事,据村民李成章回忆,因侵略者绘制地图时误将交口村标注天口村,且已制图在敌战区使用,遂依图更名。是不是这个原因已无法考证,不过现今交口村文史馆仍保留的更名前后文字资料两份。一份为民国卅年一月二十四日村民会议给村民冯堂兴的通知书,上有:“離石縣第一區交口村圖記”公章一枚;另一份为民国卅年十二月一日村民冯堂昌,杜德昌纳税收据一张,上有:“離石縣第一區天口村屠畜稅務征收分局”公章一枚。新民小学学制四年,有国语、算术、常识、日语、音乐、美术。村副付玉卓任学董,离石陈世旺为教师。为达到奴代教育目的,每星期离石的日本教师便带翻译来一次交口新民学校,对学生日语水平进行测试,带学生坐汽车兜风,欺骗学生将来去日本留学深造,极力鼓吹日中亲善。
交口村年解放,到年6月时,全村人口情况是:村户,口人,学龄儿童61名,而失学儿童多达20名。从柳林县档案局保存的年5月3日离石县第一区各村学龄儿童调查表看,当时全村有男童7-9岁6名、10-11岁1名、12-13岁9名、14-15岁10名,共26名。女童7-9岁20名、10-11岁6名、12-13岁6名、14-15岁3名,共35名。成分:贫农17名、中农41名、富农3名,共61名。已入学儿童数,男童25名、女童16名,共41名。成分:贫农11名、中农28名、富农2名,共41名。调查表还特别注明造成儿童失学原因主要有两点:1、大的农忙,2、小的不懂事。
交口村先后开办过交口国民小学、交口完全小学、交口农业中学。校址也多次变迁,教室由数间发展至楼房,学生由数十人扩大到近千人。说到交口村的文化教育,我们不能不提到交口村的魁星楼。魁星楼(今不存),位于旧街食堂一带,这是交口村先人渴求知识、争辉文运的图腾,每年二月初三村人都要举行娱乐活动,这种传统一直持续至今。十多年前,因魁星楼被毁而无有栖身之地的魁星老爷,被村中佛家弟子虔诚地寄奉在旧街神楼中。
五
相传最早来交口村拓荒定居的是党姓家族,后来张、付两族相继迁入。清末民国时期交口村还有冯家、刘家、侯家、尤家等。土改前后,崔家、李家、吴家、高家、杨家、安家、贾家、杜家、郭家、蔡家、王家、贺家、胡家、渠家、翟家、樊家、白家等相继迁入交口。这些家族,历经数代,除党家后人已不存外,各个家族人丁兴旺。各大姓氏,有的同姓不同族,有的同族不同支。汾州府永宁州同南都八甲张氏一族,何时何地迁入交口已不详,据村文史馆收藏的《离石交口张氏家谱》讲,始祖张世华起至今已历余年,繁衍子孙16代。谱中还讲康熙、雍正两朝,文臣武将,路经交口,离轿下马,诗词往来,极尽恩宠。
交口付氏六门为始祖付国聚之后代,自陕西永郡迁来中阳道棠村,至今已历六百余年。付焕居交口,生四子:金贵、金照、金礼、金义。其祖父付兴延为始祖12代传人,兴兄弟8人,排行为6,故交口付氏历来就有6门之称。现交口村文史馆就保留有付氏年3月8日制《傅氏居交口第六门宗谱》。
冯氏先祖冯州秦,居石州马茂庄冯家沟,百年后下葬于马茂庄鞋帮芋,距今已有多年的历史,先祖生一子名世温,世温生八子名宗道、宗义、宗善、宗勇、宗温、宗良、宗恭、宗俭,俗称“冯八户”。其后人广布离石、中阳、方山、临县、汾阳以及河南怀庆府等地。交口一支为孔家山冯自兴之后人。光绪十六年(年)冯自兴第八代后人冯满俭带着六岁的长子冯堂祥、次子冯堂学一家四口迁居交口。现今交口村文史馆就保留有山西省冀宁道离石县宣阜坊九甲孔家山冯户置“清乾隆三十二年立谱民国二十六年二月二十四日再续的《冯氏七门家簿谱》”以及年冯润泉纂修的《离石冯门八户族谱》各一本。
交口村各家族之间在生产活动中,有合作也有分歧,但合作是主流。各大家族齐心协力,共同为交口村的繁荣做出了贡献。从文史馆保存的资料看,清末至民国时期,交口村村务基本由付家主持。交口村文史馆地契资料显示,光绪三十一年交口编村村副(付光清)、民国十年村副(付光清)、民国十六年(付能显)。另据村民刘根年回忆:民国19年前后,先后有付玉廷、付能逢、付能忠、付玉山等主持过村务;抗日战争期间主持村务的有付玉连、付玉卓、付玉环等。
六
年10月,离石县土改全面铺开,上级工作团在胡克实的带领下进驻交口村。村干部一律停职,只有三名党员参加了贫农团。贫农团以吴补牛为团长,李根喜、付三虎、杨银三为成员,侯守敏为代表会组长。在工作团的领导下贫农团发动群众,划分阶级成分,斗争地主恶霸,经过土改,基本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目标。
(胡克实旧居)
交口村年建党。从年起死亡、外调、参军、开除党员共18人,年6月整党前全村有党员20名。整党时首先召开代表会、贫农团会议,宣传整党政策和意义。其次,找党员个别谈话,摸清思想,多数党员对土改中被撇开有情绪,发牢骚,说:“当家三年狗还嫌”,“去年党员就像私生子,”“革了几十年命,连进贫农团的资格也没有”等等。第三,针对党员思想,组织学习毛主席《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宣讲党的斗争历史,回顾减租减息、回赎土地、反讹诈、土改、解放离石等,引导群众、党员认识党是为穷人服务的。教育大家看清形势,打消情绪,端正为人民服务思想。部分党员检讨了过去作风不民主,打群众、偷西瓜、分好地,包庇地主等问题。会上据县委指示,提出了入党五个条件:1、本人历史好,为人正派;2、参军参战,爱护军队;3、工作积极,斗争坚决,努力生产,跟毛主席走;4、热心为民,办事公道,联系群众,不贪污;5、服从组织,遵守纪律,缴纳党费。妇女另加两条:1、作风好,家庭和睦;2、劳动好,不懒惰。经过学习教育和老党员贫农团、部分中农参加的大会评议、审查,从21个申请人中通过了18名入党对象,报区上批准为15名,(男11名,女4名;贫农13名,中农2名),并填写入党志愿书,举行了入党仪式。并由新老党员和工作组八人,组成整党委员会,编了5个党员小组,女党员另编一组。民主选举产生了小组长,通过了支委名单,召开群众会进行审查。经过整党,党员干部更积极了,组织修多丈长的水渠1条;带头入股开了1座油坊;办了1个合作社;圆满完成了夏借公粮任务。
七
交口村的地名,有以自然地理命名的、有以人文元素命名的、有以姓氏命名的,也有以功能命名的,它们既是当今地名,也是历史地名,大部分都有悠久的历史。交口村的村名是因川水路相交而得名,据离石区红眼川乡西山里村《重修虸螯庙记》碑刻记载,早在元至正六年()就有了交口村的村名。交口村依山就势分布在太军公路(国道)的两侧,按照吕梁市的规划这条路叫兴南路,上年纪的人仍把兴南路分成两段,在南的叫阳湾,处北的叫背湾。沿着弯弯曲曲的兴南路,向东有好几条不是很深的沟,叫法师沟、沟里、油坊沟、圪针沟。从高家沟娘娘庙到交口,第一条沟叫法师沟,法师沟的沟掌被称为风嚎洼,相传古时候沟里有巨蟒作祟,从一个嚎字,可见风的大小与诡异,后来请了当地有名的法师方才安定下来。风嚎洼的山顶有一座圆圆的土墩,叫墩梁,古时有“五里一墩,十里一堡”的说法,可见墩梁就是当年的烽火台。墩梁之上有个制高点,抗日战争时期鬼子在这里修了一座碉堡,于是村里人就把它叫成碉堡梁,阳山上的武工队员姜生山就是在碉堡里被鬼子活活砍了十八刀而牺牲的。碉堡梁的下边有一块圆形突出的地,叫圆各垴,圆各垴的下面有一块地叫坪各垴,现在建成了一个山上观景台,站在这里,离石、柳林、中阳,千山万壑尽收眼底。
交口村的人主要集中居住在几个区域,背湾这边有背崖、张家上和瓦窑上,再就是巷巷里和崖上。日军侵华时期曾在崖上设过“红部”,交口村的付成孩就因红部伏击战而牺牲。巷巷里是交口村人口最密集的地方,巷巷里不是一条街,而是几条互相连通小巷的总称。巷巷里出来就是交口村的旧街,旧街上原有两座门楼,南北对峙,一座叫魁星楼,一座叫神楼,两楼下边均有门洞供人通行,两楼之间的街道便是民国以来传统的商业区,后来魁星楼被毁,神楼的门洞因地形抬高被土掩埋。阳湾里古槐树一带,叫沟里,也叫付家大院,付家是民国时期离石有名的士绅之家,老人们说:出离石南门要数付家有钱,方圆三十二村都有他家的田地,家里养着几十槽骆驼,平时还养着一把(8匹)骡子,一年四季专门拉运租子。沿沟里往上走,还有一条小沟叫枣沟里,想来这里曾经有好多枣树吧。沿着枣沟里再往上走,就是山神庙,山神庙下有个地方叫乱坟茔,说是专门用来埋葬那些无主的死者。乱坟茔附近有个地方叫书房洼,这里曾经出土过汉画像和明代刻有楚庄王赠只将军的铭柱,老人们说早些年这里还有几个土窑洞,相传曾有人在此读过书。我想这些读书人该不会就是那位只将军的守墓人吧。龙王庙建于何时已经没有人知道了,付家西院里就位于龙王庙附近,县河的河道原本在靠韩家坡,圪垛村的一边,交口这边还有好几百亩的土地,村里人习惯把这一带叫庙坪上,后来因县河水改道,洪水把龙王庙、西院里推得一干二净,还把民国十年修的一座石拱桥推得只剩下桥墩子,为了通行方便,人们把筑桥墩的石头铺在河床上,叫作平桥。州河的旧河道相传曾到过背湾石角底(旧派出所拐弯处),县河与州河在交口村相汇后,把水久滩这块湿地也变成了一块盐碱地,靠近州河的地叫中滩上,上河滩,小河滩。水久滩与中滩上在20世纪90年代建成了一个拥有数百间门店房的商业区,人们习惯把这里叫商业大街,年温家宝视察交口村时称商业街为“北方农民城”。现在这里又建起了十二栋楼房,叫新农村住宅区。桥头起有种“蓝”的历史,“蓝”是一种植物,可用来染布,因此这一带也叫蓝池上。油坊沟是因为有一座历史悠久的油坊而得名。圪针沟的大名则与沟里有许多刺人的小酸枣树有关。据说圪针沟曾有过野猪出没,这是可信的,因为山上就有山猪洼和狼窝甸的地名。胜利池是建在葫芦塔上的,蛇腰圪嘴和葫芦塔一样也是因地形而得名的。党家据说是最早在交口村开荒居住的家族,比交口村的老张家还要早,现在党家的后人在那里已无人知晓,不过胶泥沟一带沟梁上仍有几间土窑洞,冯常山老人在世时说,这里就是党家曾经住过的地方。父亲说,他们小时候,曾在这里挖出四四方方的一些土坑,里边用白灰涂得平平的,大人们说那是米仓、粮仓。没有人知道党家住过的地方叫什么,于是我们就给这里起了个新地名,叫党家洼,也算是给党家人做个纪念吧。
交口村的许多地名像交口的许多人和事一样,无可奈何地走进了历史,不再被人们所知道,不过有些地名仍以其无可代替的地位继续被村里人沿用,当然也有新地名不断出现。年按照交口街道办“村改居”和“党建”工作的要求,交口两委本着尊重历史、兼顾当下、凸现特色、反映地理、好记顺口、规范有序的原则,将交口村分为阳湾区、朝阳区、古槐区、兴南区、泰安区五个管理小区。
八
悠悠岁月,犹如一条奔流不息的历史长河。点滴往事,仿佛是长河中溅起的几朵浪花。我们都是历史的过客,昨天、今天、明天,交口村发生的故事,都将汇入这条长河,永不枯竭,一直流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