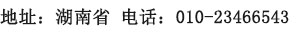留学低龄化、“掐尖儿”官方化……谁在撼动国之根基?
刘加民
最近被一个新闻惊到了:我们在英国有1.5万小留学生,因为遭遇疫情需要回国。这些小小年纪就远赴重洋到异国他乡独立生活的孩子们,忽然之间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出现在世人面前。一方面,我要佩服这些孩子的家长:他们是秉持了什么样的教育理念,舍得把这么小的孩子送出去?另一方面我有很同情这些孩子:在最需要父母陪伴的年龄,却要寄居在外国人家里,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享受所谓“先进”的教育,需要承受多大的心理压力?在中国孩子到海外留学低龄化对家庭、个人与社会可能产生的诸多负面影响完全没有解决方案的情况下,已经有这么多的家长勇敢地开始了伟大的冒险,相信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
请注意,这仅仅是英国一国,仅仅是小学生,就有1.5万之多,那些去了欧洲其他国家的,去了加拿大、美国的,还有澳洲、新西兰的,那些年龄较大的大学生研究生,又有多少呢?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这些年,发生了什么,让我们的国之根本发生了偏差、动摇,用曾经流行的话说,谁在挖社会主义墙角?
一、谁是中国教育失败论的获益者?
在教育普及的现代社会,人们不是被教育“成全”了,就是被教育“祸害”了,完全不被教育影响的人,几乎不存在。正因如此,几十年来,在中国,吐槽教育都是最广谱的话题,似乎人人都是专家,个个都是内行。越来越多的留学回来的,或者想留学而不得的人,充当起了海外留学的义务宣传员。所谓专家学者,所谓各个档次的媒体,都不约而同围绕教育做话题、做节目,而这写话题和访谈节目,几乎无一例外是吐槽中国教育的。有意思的是,当有人给中国的基础教育一点正面评价,立刻就如踩了猫尾巴一样,引来各方面公知大V的围攻和嘲笑。比如十年年物理学家杨振宁说“中国的基础教育不比美国差”,引起轩然大波,至今余波未平;比如央视白岩松说北大清华培养的人才绝大多数送给了我们的竞争对手,立刻就有人用科学无国界的陈词滥调来反驳。
这种一边倒的,只允许说中国教育差、西方教育好的的舆论,几乎成了一个思维定势。言必称西方教育,成为了很多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比如关于应试教育。据说西方是素质教育,把个性化和创造性放在最重要位置,而中国相反。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是对立的。但是仔细想一下会发现,道理未必如此简单。考试是人类选拔人才的办法之一,至今没有过时。中考、高考仍然是中国也是全世界最好的最公平的人才选拔方式之一。如何把握这个分寸和尺度,是见仁见智的事情。那些来自世界各国,能够通过考试取得到西方发达国家重点大学读书的机会的学生,基本上都是在自己的“祖国”名牌大学里最优秀的学生,他们是以近乎满分的成绩“考试”进入国内的大学,又以近乎满分的GRE、TOFFLE成绩“考试”进入了美国的大学的。因为考试也是一种能力。考试题目的创设,也是一门很高深的学问。试卷本身就已经包含了丰富的“选拔学”智慧。每一个题型的设定和不同题型的分配,都不是随意为之。
终于有人披露了这样的事实:在哈佛、耶鲁、剑桥这样的顶级大学,图书馆是24小时不打烊的,凌晨三四点钟,也依然灯火通明。这种寒窗苦读的感人情景与很多中国人对西方大学的想象,大相径庭。因为我们习惯于把一般公立大学、社区大学的自由散漫当成了西方大学的全部,忽略了他们的等级和类型,也忽略了“宽进严出”的西方大学教育的传统。当我们以“素质教育”的名义放弃的,正是西方重点大学孜孜以求而不得的,不得不全世界筛选的。批评中国基础教育不行的人们,还喜欢这样的故事:某孩子在国内成绩很差,到了西方就变成了优等生,因为他们更加重视个性,教学方法更先进科学。我觉得未必。一方面是教育评价的标准不同,得出的结果自然也就不同。另一方面是那些主题先行的教育专家,选择性遗忘,可以回避了不符合自己观点的教育案例。而对那些招生困难的野鸡和半野鸡大学而言,这样的“励志故事”,与其说是西方教学方法有点石成金的神力,不如说是他们的招生宣传手段高明。
最近几年的形势,又有微妙的变化。中国的崛起事实上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秩序,但是中国所承受的来自竞争对手的压力,和来自国内国外的负面评价,关于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也早就位列“批倒批臭”的名单之中,甚至“中国教育失败论”都出来了。自费留学的越来越多,因为有钱了;低龄留学也升温很快是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基础教育不好。看不起中国的基础教育且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毫不犹豫选择了远走高飞。没有条件出国上学的孩子怎么办?他们看不起自己的老师,家长不理解老师对孩子的严格管教,他们一千个不情愿,一万个不服气,憋憋屈屈混迹在中国的校园里,制造出一次又一次师生冲突。可是,如果中国的基础教育真的不好,为啥那么多中国学生轻松愉快考上美国的名牌大学?如果中国的教育体制压抑个性、排斥创新,为什么那么多中国留学生把美国的考试卷子也做得甘之如饴、哗哗作响?
从英国1.5万小留学生迫切需要回国躲避新冠疫情的“新闻”,我们终于可以非常直观的看到,说中国基础教育不行的人们,那些媒体人和专家学者,终于打造出了一个时代的尴尬和荒唐:
这就是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把孩子送到西方留学,接受西方教育,享受西方文化,根植西方价值观,而且越早越好。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空有一副中国人的皮囊,而内心深处早已经背叛了自己的文化,自己的祖国。重视教育是中国人诸多优良传统之一,利用这个中国人最大的软肋培育教育产业的市场,毫无疑问是最有效、最精准、最具潜力的。这些小留学生实际上都是一个个小财神爷,英国的留学费用是最高的国家之一,每年四五十万人民币是很正常的开支,加上往返机票和各种日常开支,普通的工薪家庭十分吃力。但是对于接受中国留学生的国家的教育产业来说,随着一批一批小才神爷的到来,毫无疑问,教育产业也可以像军火、能源、操纵汇率等一样给欧美发达国家的人民创造福祉不是?
一方面是文化入侵从娃娃抓起成为了常态,一方面西方以中国孩子为“客户”的教育产业蒸蒸日上,鼓噪中国教育失败论的最大受益者,是西方国家。
二、准许西方到公办学校“掐尖儿”符合谁的利益?
如果你认为,几十年如一日为西方的教育产业殚精竭虑、添柴加油、为西方国家输送人才的,是极少数人的个人行为,是某些特殊群体的突发奇想,那就特错特错了。他们是以政府之力、持之以恒、推动了几十年的。
如果你认为选择适合自己读书的国家和学校,纯粹是公民权利,政府不应该过度干涉。那你大错特错的,公民权利是以爱国主义为前提的,那些从小接受别国教育孩子,长大后就成了外黄里白的香蕉人。
几十年来,中国基础教育在舆论和各界大咖的吐槽中艰难前进,“崇洋媚外”的教育理念催生了越来越多的反常现象。偶尔也会被中央批评,被有识之士揭露,也会有教育行政部门发布一些加强管理之类的不痛不痒的通知,比如合作办学、国际学校、公办学校里的国际班、如何选用外国教材等等出现的问题。遗憾的是,这些“无效的管理措施”,都如同蜻蜓点水,雨过地皮湿,完全不能与愈演愈烈的“人才掐尖儿”工程抗衡。
君不见,多年以来,全国各地的重点高中校园里边,雨后春笋一般出现了“国际班”,准许发达国家在中国的公办学校校园里开辟“小特区”,把中国最优秀的孩子提前“圈”进来,用西方的教材和理念培养三年,高中毕业不用参加国内的高考直接进入美国的大学。这种为西方教育理念和人才培养大开绿灯的现象,这种“单向国际化”的半学理念支撑下的办学机构,早就从一线城市、二线城市,向三四线城市快速扩展、蔓延。甚至连最偏远地区的商业楼盘,也以引进了英美教育理念的学区房为荣,以开办国际学校、双语教育、外教教学为卖点。把中国最好的孩子,这些连北大清华都看不上眼的孩子提前送给欧美发达国家,其中奥妙早就超出了“基础教育”孰优孰劣的一般性比较这么简单了。在大批民族品牌快速消亡的全球化时代,在非常可乐、健力宝、汇源、美加净、牡丹电视机被外资猎食并快速消亡的时代,教育问题早已经不是教育本身,它不可避免与经济问题相钩连,甚至与地缘政治也大有关系。
秋天,我发布了《美国对中国的人才掐尖儿已经从高一开始》一文,引起不小轰动。触发我感慨的是朋友家孩子的故事。朋友的孩子考上了北京某重点高中的国际部。春节聚会的时候,这个才高中第一学期的孩子,刚刚结束了寒假美国游学回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已经是一个言必称美国的小洋奴了。这个孩子眉飞色舞地说,他们班50个学生,高中毕业百分百会进入美国重点大学读书。他的志向是读医学,留在那里。据我了解,北京最优秀的11所高中学校(市级示范高中)都有这种“国际班”,专门为国外重点大学培养人才。这批全北京最最优秀的学生,这批连北大清华都看不上眼的孩子,家庭条件优渥的孩子,从高中一入学,就提前进入了美国高校的“预备班”。美国人对中国人才的“掐尖儿”,提前到了高中一年级。
这种高智商的孩子,如果被洗脑,是非常可怕的。网络媒体上一直流传着一个经典案例。年,清华毕业的女生高杏欣,赴美留学后轻松破解了中国北斗星的密码,得到了美国国防部的表彰。中国政府十分尴尬,赶紧修补。从理论上讲,美国成功破解他国编码程序后,就可以通过先进的电子拦截设备捕捉其导航信号,以分析外军部队调动或者武器装备的具体位置,进而通过GPS确认这些数据参数,也能在需要时对导航信号进行干扰。在最坏的情况下,破解别国的卫星导航定位编码后,美国军队指挥官将和外军指挥官一样,对外军的军事部署和装备位置信息了如指掌。这对别国未来的军事行动显然有很大影响。
美国是一个高度重视人才的国家,这个已经成为他们的优良传统,并且传承不断。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之后,美国有一个人才引进工程,那些在欧洲生存困难的科学家,被廉价吸引到了美国。众所周知的钱学森归国的故事,就是一例。据说,当时周恩来总理,亲自交涉,希望钱学森回国参加两弹一星建设。让美国大伤脑筋。他们对这个他们“宁可失去三个步兵师”不舍得放弃的人才,设置了重重障碍。奥巴马上台不久,就到一所中学访问并发表演讲,他敦促孩子们好好学习,不怕吃苦。“否则再过二十年,你们就只能给来自印度和中国的孩子打工了”。这些年国内大学的生源争夺,早已经如火如荼了。各省市高考状元的资料都被大学提前圈定。港、澳、台大学也取得了通过内地高考,选拔优秀学生的权利。但是美国更绝,他们直接在中国最优秀的学校设置“国际班”,从高一开始,就把智商最高的孩子圈下来。
历来高度重视人才的美国,从自己的国家利益出发,全世界花样翻新搜罗挖掘抢夺人才,可以理解。我有点不明白的是,这个美国政府提前进入中国中学校园,进行人才“掐尖儿”的工程,竟然得到了中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一路绿灯,畅通无阻,而且规模越来越大。毫无疑问,这是自毁长城的祸国殃民的政策。在美国时时刻刻绷紧了人才战略的弦,想方设法从全世界各国笼络最优秀人才的时刻,中国教育官员却反向行动,送货上门,国门洞开,双掌朝上,把最优秀的孩子们恭恭敬敬送给美国。中国没有自己的人才战略吗?中国的国家利益不需要保护吗?美国人时时刻刻把自己的国家利益放在心上,中国人却把美国的国家利益当称自己的“国家利益”,这种伟大的吃里爬外的精神,这种毫不利已专门利人的教育汉奸行为,不是发人深省吗?改开四十多年,我们把物质财富输送给别人,那是国际贸易,那是互惠互利,说白了对方赚大头我们赚小头,那么把最优秀的人才无条件地送给别国,就属于自掘坟墓。
还是回到最近发生的事情上来:
除了1.5万在英国的小留学生哭着喊着要回国躲避瘟疫,引发了一系列争议,暴露了一大堆深层浅层的问题,刺激公众神经的还有一位公费留学生许可馨,这个年被中国药科大学推荐至美国德雷塞尔大学公费留学,貌似品学兼优的学生,却在近些天多次在网络中公开对国家和国人进行诋毁辱骂,并且坦然自称是“恨国党”!还有成都电子科技大学赴美做博士后研究的麦文鼎,公然不顾事实和后果,在国外的社交媒体上公然承认新冠病毒来自中国,并代表中国向美国道歉;青岛的某个孩子回国后,叫嚣“我是中国籍,但早就不是中国心”,还有年5月21日,在夏季马里兰大学毕业典礼中,中国留学生杨舒平代表中国留学生进行发言,跪舔美国,抹黑祖国的无耻言行……
总之,对国家、民族而言,教育决定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事关国家的兴衰,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我们坚持“四个自信”,更基础更深刻更广泛的是文化自信,文化“腐败”的危害更为隐蔽,也更加危险。教育的天职是传承优秀文化,教育是为文化自信服务的,是意识形态斗争的重镇,在千年不遇的国际秩序大调整的关键时刻,如何打造并掌握住一支忠于祖国和人民的优质人才队伍,中国人要把教育掌握在自己的手上,用我们自己的传承五千年不断流的开放又包容的优秀文化教育下一代。
抛开真实与否的纠结,看效果
刘加民
用“效果”评价文学作品,并不是一个新鲜的提法,早在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结合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现实斗争的需要,明确提出了看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的观点,即判断一个作品的好坏,看动机,更要看效果。
毛主席指出:“我们判断一个党、一个医生,要看实践,要看效果;判断一个作家,也是这样。真正的好心,必须顾及效果,总结经验,研究方法,在创作上就叫做表现的手法。真正的好心,必须对于自己工作的缺点错误有完全诚意的自我批评,决心改正这些缺点错误。”又说,“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即其动机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主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
显然,毛主席是站在以现实主义文艺为主线的中国文艺的历史纬度上,结合文学作品对现实关照的广度、深度以及作者的主观意愿所达到的程度,对文学艺术尤其是文学作品进行评价的。这个评价标准融合了文化传统,经受了革命文艺和改革开放的当代文艺实践的考验,在几代马克思主义文艺工作者手上传承至今,依然没有过时。
冲击“效果标准”最严重的是“真实标准”。“说真话”是广为接受的文学作品评价的至高标准,是追求“善”与“美”的起点,离开了真实,一切都会变成镜花水月。标榜并且追求真实,是很多作家艺术家乐此不疲的事情,不论他是什么党派,阶级的立场在哪里。
细究其实,却可以发现一个让人懔然而惊的微妙。什么是真实?真实是不是唯一的?文学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真实比之于现实生活本身的真实,有什么不同?窃以为,基于现实的真话,是最大限度描述不走样;基于内心的真话,是排除干扰不说违心话。而真实也有表面局部的真实和本质整体的真实的区别。那么,作家艺术家顶礼膜拜的“说真话”,是基于哪一种真实呢?
从接受美学讲,不论哪一种真实,只要作为一种文化产品,就要考虑受众的理解和可能产生的后果。“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通常指的是读者因为自己学识、经验、立场和社会环境的不同,而对哈姆雷特人物及其故事的理解有所不同,甚至完全不同。比如方方日记,关于疫情防控这一部分现实的描述,显然是真的少假的多,因为她没有一手资料,都是无法查证的道听途说。关于内心真实,我想基本上都是真的,因为她作为一个新写实主义小说作家,多年来始终坚持反抗现实、揭露黑暗、忠于自己内心的创作理念和实践。方方写日记,如果仅仅是私人生活的一部分,一本纯粹个人的本源意义上的“日记”,没有人可以干涉,这是她的权利。甚至如果她的日记仅仅是小范围几个闺中密友的分享,或者只是在国内读者范围内的文学交流,有辩论也是正常的,有反对也有支持我们乐见其成,我们提倡就是各抒己见、百花齐放。但是她的日记是作为文化产品进入大众传播的流程的,是在网络上向所有人即时公开的“文本”,她就必须考虑考虑这些文字内容包含着的认知、教化、审美和意识形态等功能所能达到的边界,考虑这些文字可能衍生出来的诸多不利于抗击疫情的负面作用,考虑到在全球互联的时代这些“日记”所一定会产生的国际政治的影响和效果。因为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清晰地看到了,方方日记不仅同步传播到了国外,收工之后还被作为独立的出版物被授权给了国外进行出版发行,被加工制作成了某种国际政治斗争的工具。这时候就要看是谁在喜欢这些日记,他们想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国外的传播与国内的传播达到的效果有什么不同。
鲁迅杂文《立论》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一家人家生了一个男孩,满月的时候抱出来给客人看。有人说“这孩子将来要发财的”,得到一番感谢。有说这孩子“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他于是得到一顿大家合力的痛打。说明讲真话还要有适用的场阈,所谓“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即便是百分百的真话,是忠于现实也忠于内心的大实话,也还是要考虑到传播出去之后的效果。在寓言故事《盲人摸象》里,人人都摸到了实物,都说出了自己感知到的真相,但是显然他们都只是触摸到了大象的一个局部,所以都不能正确说出完整的大象的样子。这时候,就还需要一个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相结合的——在阶级社会里还有考虑阶级的因素——认识世界表现世界的科学的方式方法。在效果评价里,还有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它的时代性。一时一地一人一事的效果,很有可能随着条件的消失而消失,这是很多很多追求现实意义而丢失了永恒意义,从而被局外人、后来人诟病的根本原因。所谓知人论事,所谓发展的历史的眼光,在这里格外重要。
总之,不论从真实与否的角度,还是从传播效果的角度,方方是用一大堆真实的“元素”拼凑出的却是一个个完美的谎言,又用道貌岸然的悲悯传播了无以复加的冷酷和阴暗。支持她的振振有词,反对她的也是言之凿凿,加上新的热点迟迟没有到来,对方方日记现象的